苏州河北岸去外白渡桥不远的百老汇大厦是中国最高的建筑,它在天空线上那样特殊。凡轮船驶向大海的时候,三个或四个小时后它的影像还是缠绵不去,直到东海之水,由黄色变为碧青,它方形影模糊。
那时候淮海路还叫做霞飞路,飞机旅行还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凡出国入国,很少人能避免上海,即使在国内旅行,也可能以上海作转口埠。当日粤汉铁路方才由衡阳向郴州伸展。我父亲从长沙家里前往广州或福州,也不经陆路,而是乘船至上海,由此漂海南行。
那是张爱玲的上海,也是茅盾、巴金、张天翼和穆时英等人的上海。孙中山在此置有私宅,蒋介石在此初次邂逅宋美龄(当日称为“三妹”),毛泽东曾在虹口码头向赴法工读的朋友告别……这些都已是往事了。30年代,五卅惨案已被淡忘。自从日本占领东三省成立满洲国以来,亲英联美成为国策与民情。租界内的公园门口的“华人免入”的牌匾已经撤去,但是上海仍离不开殖民地风味。英租界的巡捕,全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材魁梧,长发浓须。看来都是一模一样。法租界的则是脸颊凹入黑牙齿的安南人。兆丰花园附近有一座英国兵营,不时有英军整队游行过市,既敲鼓也用袋风笛作前导。那种乐调哀怨凄凉,今日回味使人想及苏格兰之荒山,遍地羊齿蕨随风起伏,不知英人如何以此等音乐淬砺士气,足以征服印度中东,进军于波斯及阿富汗。
对我们来讲,上海则是中国的文化城。人家也说北平(当日不能说北京)是中国的文化城,但是那座古都除了三十多家大学与学院之外,很少与一般民众保持接触。上海则有各种报纸杂志期刊。我们所用中小学的教科书,出版社总是商务、中华,以后的生活新知也在上海露像。郭沫若(还没有人称之为郭老)在这里发行创造社的各种刊物,自己则避祸于福冈,鲁迅在国民党清党期间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抗议,以后仍寄居闸北,经常与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过从。他们的闲谈也见于鲁迅之笔墨。他在本地《申报》辟有专栏。黎锦熙提倡汉文拉丁化,首先在福州路张开布幔,大书“大炮响了”。林语堂在北京还是循规蹈矩不离主流,及至上海才主张国难与否,人生总要追求生活之情趣,从此成为“幽默大师”。
上海也是一座国际城市。不时有欧洲水手,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去外滩不远,大概是九江路或汉口路的酒吧间群殴。有一次事后捡拾,除了损坏的桌椅杯碟之外,还留有撕下的耳朵一只。
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tin在这里与出版者兼作家邵洵美同居。当时邵已是有妇之夫,但是无伤大雅。项仍然将她的经历写入《我的中国丈夫》。以写《大地》而闻名中外的赛珍珠生前将绯闻缄锁,但是她去世后,为她写传的作者发现她也有一位中国情人,此人乃诗人徐志摩。他们的邂逅,也在上海。
而且上海出产所有的国产电影,对内地年轻人的影响无可衡量。金焰,王人美、胡蝶、徐来,成为了众人倾慕的对象。《渔光曲》与《大路歌》都是影片中的主题歌,一经播出即引起全国风诵。还有《义勇军进行曲》原为《风云儿女》影片中之插曲,预期有歌词二首,但刚写完第一首,作词者田汉即为国民政府的法警捕去,寄押于苏州监狱。作曲者聂耳只得将所作词重复一遍。也料不到这部电影中之插曲在抗战期间同为国共两军之军歌。以后更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提及电影,使人不能忘记阮玲玉的悲剧。她与张达民还没有办妥离婚手续,即与茶商唐季珊同居,被张在法院里控告通奸罪。她被逼自杀,还留下一封绝命书,“你虽不杀伯仁,伯仁却为你而死。”结尾重复写出:“只不过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噩耗传来,不免使我们一代年轻人惋惜。据说她装殓时仍是风采妍然。与项美丽相较,她真可谓重誉轻生了。
这样的文物与习惯,没有体系与合适的逻辑。静安寺路外人称为 Bubbling Well Street,直译则为“出水泡之井的街”,而在十里洋场之中也真有一所寺院,不时有信男信女前往膜拜进香。上海虽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在墙壁上以丈尺大字写出的商业标识不是雪佛兰轿车或奇异GE电气用品,而是当铺之“当”与酱园之“酱”。法租界与中国南市交界之马路称为“民国路”,也从法文译来,原文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道路”。因为分界线在街心,所以彼此各发通行公用汽车之执照。乘客必须注意:由东向西行必乘中国汽车,回程由西而东则须换乘法国公司之公共汽车。
众人都说凡世界上所有新出品,本地尚不能买到,立即见于上海。沪西的住宅区也确具有欧洲城市情调,但是各处弄堂仍然门前生火炉,临街泼秽水。霞飞路之法国梧桐点缀着酒吧间和咖啡店,不失为拉丁区。北四川路则为日本人的世界。一至午后放学钟头,电车上全是日本学龄小孩,他们顽皮嬉笑。全新的白色帆布球鞋,也用毛笔大书物主姓氏,如“北原”,“冈村”。只有南市始终不失为中国城,仍在等候20世纪的来临。虽然搪瓷工业已经高度展开,此地仍生产木质器皿,而且店铺与工厂不分,许多商店临街打造。中外商品之不同,也可以从所用的溶剂分别,惠罗公司所陈设的欧洲货品,多具芳馥之气,因为所用松脂油和棕榄油大都经过处理。中国土产则多具原始的桐油与靛青的气味。
纵然上海有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物使我们丢甩不开自卑感,但是与内地相较,“海派”仍然是摩登与进步的表现,这时候中国的女学生已学会涂口红。年轻男子所服用的knickerboker,称为“灯笼裤”,我在长沙中学时也和同学服用土布制模仿品,其来源也由自上海,沪上则抄袭西方,有《字林西报》的广告为证。
因为操沪语的人总是得风气之先,要较我们遇事内行,我们对这种方言也颇为倾慕。尤其海话(读如偕窝)中之特殊字汇,好像隐蓄着不能形容之奥妙与魅力。凡事物犀利漂亮则为“灵光”,否则即是“蹩脚”。潇洒不务正业者为“白相人”,穷措大之尊称为“瘪三”。笨蛋号“阿木灵”。事物之程度,以“邪气”或“交关”表示。钱钞概为“铜钿”,小二则称“烂污泥”,出租计程车为“野鸡汽车”。之乎者也矣焉哉之。“哉”字原只见于《四书》,在此地则出现于任何人之口语,有如文墨之有惊叹号。能说得一口流利沪语是如何的“帅”!为着追求这种说不出的风味与情趣,我曾想加功练讲。不幸天生“大舌头”不能及时辗转,越想苦学愈不灵光。眼见他处来的孩童只三数日即全部吴侬软语,令人不胜艳羡。
(摘自《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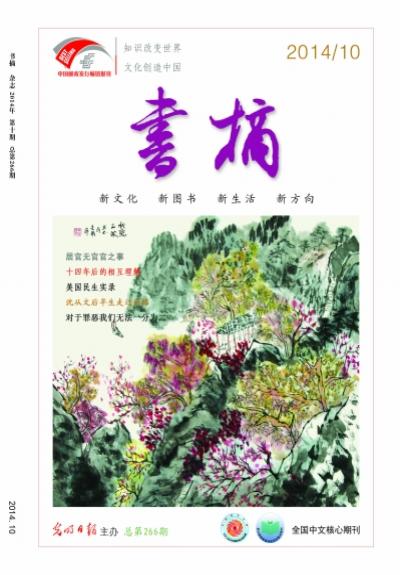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