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民间粤语,常用一个“搞”字:“有冇搞错”、“搞掂”,而内地官方用语有一阵子也用“搞”:“搞革命”、“搞生产”、“搞男女关系”。倒是台湾人好像是本来不怎么搞的,可能正是如此,台湾音乐家罗大佑在上世纪90年代移居香港后,大概整天听到香港人搞这个搞那个,遂想出“搞搞新意思”这样的歌词,这用法并不是香港固有的用法,但香港人也乐于接受。
能广为流传的方言用词大概反映了地方的特色,特别是地方的强项,譬如早就流行全国的广东话是“生猛”,反映广东人的爱吃,特别是吃海鲜。现在内地有些年轻人学周星驰说“我走先”,也反映香港电影一度的强势。
北京人很喜欢说:是吗?譬如我说:你叫我办的事,我办好了!北京人会回应一句,是吗?他并不是在怀疑我。但许多地区不习惯说“是吗”?他们喜欢说“真的”?台湾人就特爱说“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北京人对着台湾人说“是吗”?说不定有些台湾人会以为北京人在怀疑他。有时候语言引起误会还真容易,是吗?真的。
两岸三地的中文情况是:不完全一样,但也不会完全看不懂。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搞电影,香港电影都有中文字幕的,那时候台湾市场很重要,除了国语版请香港说国语的北方人配音外,字幕也是请那些操国语的中文比较好的香港北方人,把粤语对白改写成国语字幕。我们以为做得很周全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台湾连说国语的外省观众都一直觉得我们香港电影里的字幕有点怪怪的,原来香港说国语的人的标准中文跟台湾说国语的人的标准中文已经是不一样的。
我常发现用中文写作的香港人,心里面往往有个阴影,怕自己的中文不够标准、不够正宗,过去更曾经有学者拿这来说事,鼓吹所谓纯正中文。香港不少文化精英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中文纯正化,因此也最焦虑。大陆台湾固然也会试着规范中文,但只是为了用字符号的标准化,而不是怀疑自己的惯用中文是不正宗的。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结果,看看两岸应该是最规范的书面语,那些公文,官方文句,还真的不太一样。
香港的作家是挺可怜的,你看看许多香港的小说,里面的人物明明是当代香港人,但他们的对白,基本上是白话文国语普通话,而不是现实生活里他们身份应说的生猛广东话。
这方面北京作家心里最踏实。那些写现在的北京的小说家,把北京的流行话语都写在小说里,从来没想过其他地方的人看不看得懂。老舍这样做,叫京味,到了王朔叫新京味。有一次我说,你们北京作家多幸运,说得出就敢写,别人看不懂就得学。他们说,还真没想过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可怜地方上的中文作家,要在上下文自明的情况下,在想象的标准中文书面语之下,加点特色方言俗语,作为风味点缀。对地方作家来说,写作中的方言俗语只能适量,多了其他地区读者就看不懂,有点像改良过的地方风味菜,太原汁原味倒怕别地方人不爱吃。
不过,在上世纪白话文建构之初,却对方言文学另有期许。当时有人说:
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白话文的创导者胡适(《吴歌甲集序》)。
甚至到了一九三〇年,胡适还在替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写序,他说: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
他又说: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国族的白话文国语倡导者竟如此肯定地域特殊主义,实在不可思议,原来白话文要替代的是文言文,而不是针对方言,并且方言是被认为可以丰富白话文和国语写作的。
胡适对方言文学的肯定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方言文学寄望过高,方言文学在中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并没有如胡适所料地扮演重大的角色。但有一点可看到,在胡适一九三〇年的观念中,白话文和国语并没有一种不变的标准,没有预设一种其他人只准模仿、学得最像者得最高分的所谓正宗中文。胡适所持的是一种动态发展观,期待着中文的演变。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觉得有责任将胡适认为“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海上花》改写为国语。她在“译者识”里说:“全部吴语对白,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个,没人敢再蹈覆辙……”
全部吴语对白,没人敢再蹈覆辙,可见哪怕是最杰出的方言小说,要让更多人接受,还是要翻译成国语。
不过张爱玲还带着跟胡适一样的一厢情愿,她竟说:“……粤语闽南语文学还是生气蓬勃,闽南语的尤其前途广阔,因为外省人养成欣赏力的更多。”
张爱玲是中文写作的大家,却对方言文学有着错爱,只是她也高估了地域方言阅读的习惯,事实上,虽然台湾有人提倡土语写作,但粤闽方言文学怎么看都说不上生气蓬勃。
纯方言的写作会赶跑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说那种方言的人。当然,个别写作人可以用任何方式写作,包括方言写作,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忍得住寂寞。
可以说,除了北京方言外,其他中文方言文学从来没有起来过。有的只是带着地方色彩的书面语写作,没有大规模的方言文学风潮。
但是两岸三地的中文仍有着很大的共通性,虽没有想象中的统一纯正,可是也没有走到另一极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或洋泾浜化至互不理解——分裂主义是不成气候的。
中文内部存在着差异和混杂,只表示了中文是活的、文化是活的。中文的转变,也表示着操这语文的人的转变。我们不能往后退,退到自己的乡村的竹篱笆内,或退回大一统的铁笼里——纯粹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应该包容、尊重,甚至享受,互相混杂却有差异的中文书写、搞搞新意思的中文。
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哈尼夫·库雷西有一篇小说的名字叫:你的舌头在我的喉咙。
没错,如果我愿意,我欢迎甚至享受你的舌头在我的喉咙,但如果我不同意或心情不好,请不要硬将你的舌头塞进我的喉咙。
总结:中文从来都是在转变中,不用过分担心中文会分裂。
两岸三地的中文是:一种中文,多种款式,可称为“多款一中”。这情况下,方言写作不可能急独,标准中文也不必强求急统,最好是不统不独,求同存异,只要承认一中,顺其自然地等时间来搞定。
多款一中的意思是:从来就是混杂和多样的当代中文,在一种想象中的所谓书面语共同标准下,并在白话文和普通话约定俗成的历史发展轨迹、读者的认受局限等多种制衡下,各地方、阶层、族群、性别、世代、载体,以至个别写作者,仍然可以有限度地作出“一种中文,各自表述”。
(摘自《或许有用的思想》,海豚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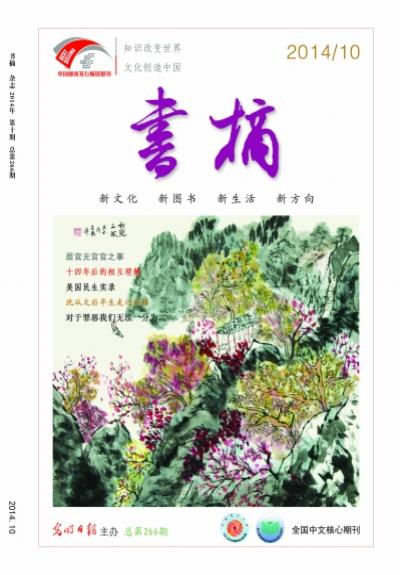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