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他(小崔)提起过一个梦。
‘我做过一个梦,梦到像白洋淀一样的地方,和朋友们在船上,能听见船桨划过水波的声音,还有水鸟从耳边掠过。’
然后他醒来,发现自己睡了三分钟。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样的夜里,一直醒着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柴静写小崔的文章《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年会“福利”
(央视)评论部每年的年会,最大的“福利”,其实是他。
他主持的联欢环节,不是亿万观众的共享,而是给几百个南院兄妹开的“小灶”。
“我们”的小崔,比其他场合放松、喜悦、尽兴。
什么“病人崔永元”,外界厚厚的粉刷,在此时纷纷飘落。
在这里,他就是一脸坏笑、没有坏心眼的同事。
他是解压阀,是黏合剂,为南院员工撑腰,奚落调侃领导,举重若轻,话中带刺,领导也不愠怒,甚至殷勤地配合着。
年会如果没了他,就失魂落魄,只剩下了瘦削的骨架。
一年年会,小崔张口说某女领导是“豆腐嘴”,下面人面面相觑,心想小崔别真接着说“刀子心了”让女领导没面子,没想到小崔不慌不忙说:“冻豆腐心。”
还是年会,他请来罗大佑,大家一起唱《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对着话筒说:“小崔,不怕,我也抑郁过,不是我们有病,是这个时代有病。”
我们盯着台上罗大佑晶光闪烁的双眼,有人说,看到小崔热泪盈眶。
那一刻,大家在心中彼此拥抱。
交集
他的公司叫“清澈泉”,他说是要打造一个心灵纯洁的集体。
严格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南院人”,而是“清澈泉”的大管家。
老六评价说,“清澈泉”听起来像夜总会的名字,但其实是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小崔的“清澈泉”公司已经成立若干年,早就在外安营扎寨。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南院西配楼三楼,还是留着一间“小崔说事”的办公室,也有人走动,像是一个“驻南院办”,情感的大本营据点。
在南院人心中,他就是南院的人文符号、精神图腾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嗅觉密码。
南院人对小崔的好感,是一个满含默契的暗号。
对他的爱护,大家心照不宣,那感觉,很像南院人常念叨陈虻。
也正如小崔对陈虻的好感。
他在怀念陈虻的文章里写:“你相信吗?这个好人走了。2002年,我在云南住院,他代表台里去看我,哄着我高兴,从此,我的病落在了他的心里。他去世前三天还对我说:哥们,你保重啊!”
小崔与陈虻之间,其实是惺惺相惜。
小崔说,从陈虻那里学到的是: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情,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点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男人尤其应该注意。
赶时髦“制播分离”,南院的主持人,要么安守岗位,要么另谋其位,小崔是个例,自己干,央视给平台。
既然自己干,就张罗喜爱和擅长的。他钻进那些易被人们淡忘的领域。 《电影传奇》、 《我的长征》、 《我的抗战》,他是喧嚣媒体中寂寞的“考古者”,却不亦乐乎。
人们都说他是个“拯救者”,挖掘老电影,抢救历史,为了和高龄老人们的生命赛跑,甚至到争分夺秒的跑步。
其实他也试图“施救”过南院的兄妹们,比如我。
2008年初,我所在的《社会记录》栏目撤销时,我和很多同事面临下岗,制片人李伦为了我们的出路奔走求援。
很快传来消息,小崔那里愿意收留我们,据说他信任《社会记录》出来的人,唯一的要人条件是,人品好。
那种感觉,好似扑腾在泳池中要窒息,一件救生衣送了过来。
但是上不上得了他的岸,还是个未知。他说要布置作业考验,写一篇分析中国电视业发展的文章。
借着他的东风,那段时间,我虔诚得像做作业的小学生,在家伏案研究中国电视产业发展。
文章还没正式写,评论部新筹办的《新闻1+1》栏目把我调了去,职业生涯也与小崔擦肩而过,但是他的那种挺身而出的侠义,也是镌刻我心头的印章。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我第N遍又看了2005年那篇惊诧世人的文章《病人崔永元》。
2005年,他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7个小时专访,那个以幽默著称的人,竟是与“自杀”抗衡的抑郁症患者,他不能抑制、词锋凌厉、愤愤批判着让他种种不满的东西,那时的他,真实也较真,不仅对冯小刚等名人口诛笔伐,对身边人的缺点也毫不隐讳。
那篇《病人崔永元》,获得《南方周末》“传媒致敬之年度文化报道”,理由是:报道既有“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等极具传播效应的精彩味道,又有关于知识分子良心与责任的深入讨论。……崔永元的困惑,恰恰折射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报道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升华。
柴静回忆2006年的小崔:
和他聊天,他谈的问题是——社会的良知的失去。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让人想要放弃……
那两年,有些东西像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那时的柴静,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只能对他说他不能放弃,“因为我们需要他。并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还有他身上的真诚和绝不伪饰,有了这个,他才有勇气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
那时,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对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心理医生说,你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也许,他此后的种种的行动,都是一种不自觉的疗伤之旅吧。
我在评论部内刊上,读到了小崔写得最长的文章是上万字的《长征——边走边想,是幸福的》,这正是他在《我的长征》阶段写的。
他记录红军们贴的可爱标语:“欢迎白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文中评点:“我觉得这个‘拖’字相当传神。”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他感怀瞿秋白的文章《1935·牺牲》。
他说,瞿秋白就义前的两万言遗书《多余的话》,他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最后一句话是: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他描述,瞿秋白在送老婆的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36岁的瞿秋白看见刑场上的绿草地,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静等枪声。
他感怀,“理解瞿秋白们所认定的牺牲,对很多现代人来说是个难题,因为这伙现代人不理解他们的信仰,不明白他们的思考结果,不认可他们的行为方式。”
他最后总结道:瞿秋白《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重走长征路时,小崔也悄悄做了一件“多余”的事。
他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一百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
这个突发奇想,也是他后来口述历史、《我的抗战》一系列行动的雏形。
他说,口述历史是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
“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
他给口述历史的团队成员培训,入门课就是先看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他说,你们先看看。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因为“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我翻阅了一下那本书,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那个年代,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成为被公开践踏的内容,留下无数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他对记者说:“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有着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时代的眷恋。也有一些人觉得“深陷”过去是种病态。
有记者问得很尖锐,说他的老电影、重走长征路,曾经的时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问他是否能把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分开。
他回答:“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小崔曾引用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一句话:“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邪”,“无邪”
一脸“邪气”的坏笑,是人们传统印象的小崔。小崔写的文字,很多也“邪气”毕露。
武侠是一种江湖隐喻的解构方式。我借“东邪”来说他,只是附会美好的东西。小崔与东邪黄药师有相似之处,从不墨守清规戒律,试图给“主旋律”作品一种新的血液。
不过,如今的小崔,“无邪”比“邪”的成分更多。
他随手公益,做慈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换课桌椅,每天微博上实时公布捐款数字、公益进展,像个认真的会计。
当年那个愤怒的小崔,那种剑拔弩张,也被岁月和心境融化了。如今,别人批评他,他不恼怒,甚至开始反躬自问了。
小崔在微博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句话:“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老崔与腾讯博友共勉)。”
(摘自《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35.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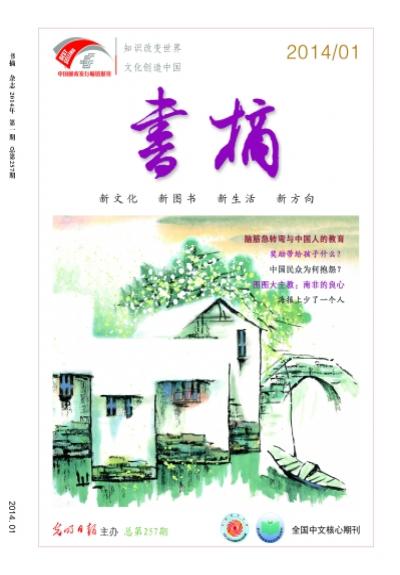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