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本身就是由于牛津大学学生顽皮闹事而形成的,剑大学生捣鬼的本领也毫不逊色,很快就惹出和牛津大学相似的事端。
教师的头疼问题:纪律
控制学生行为向来是学校管理层的要务。为了让学生专心学习,剑桥大学做到了极致。最初的手段是让学生在镇上容易识别出来,1343年参议厅批评某些学生“穿着不体面……有失身份”,并警告他们“任何人不穿学袍不准走出学院”。校方还试图让学生天黑前回学院,冬夜9点,夏夜10点,学院大门随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钟声落锁。学校把违背宵禁规定的学生称作“夜游鬼”,通常这个词指夜行动物。
一帮不甘寂寞的家伙想出了使坏取乐的新招。剑桥大学林立的尖顶和塔楼激发了无数雄心壮志,也提供了绝妙的恶搞条件,多年来成为某些学生无法抵御的挑战目标——校方的明令禁止更增添了刺激。学生的爬墙癖好也许源自宵禁后翻墙回学院的无奈之举,因为直到20世纪夜游鬼常常在深夜被锁在学院大门外。“二战”后宵禁推迟到午夜,学院大门依然要落锁,但每个学生都配发了钥匙,所以门房的职责从不让学生出去变成了不让外人进来。
长期以来,在学校爬房顶是一小帮所谓“夜攀族”学生的消遗,他们并没有正式组织,小分组之外的成员通常互不相识,因为隐秘的身份有助于躲避校方的注意。顺着冈维尔奇斯学院前面的排水管爬上去,跃过参议厅道上方七英尺宽的窄隙窜到附近的参议厅房顶,方可获得夜攀族“成员”身份。
最有名的夜攀行动发生于1958年6月7日,星期六。传说的故事并不清楚,因为夜攀族是一帮喜欢吹牛皮的家伙,但这场恶搞的结果是完全公开的:一夜之间,一辆奥斯丁小汽车竟然出现在参议厅房顶。冈维尔奇斯学院的学生花了几周时间设计了一套吊机装备,把这个汽车外壳吊到参议厅房顶,同时让参议厅建筑丝毫未损。此举博得国内外的热烈喝彩,连共产主义阵营的罗马尼亚也报道了“资本家老爷子弟”的闹剧。众目睽睽下摘取这辆车居然无比艰难,花了整整四天才搞定,让一夜之间就把车子吊上去的那几个学生偷乐不已。冈维尔奇斯学院对这次夜攀颇为自豪,院长派人偷偷给捣蛋鬼嫌疑犯送了一箱红酒,2008年吊车事件50周年庆,原团队11名成员在学院得到了盛情款待。
在20世纪上半叶夜攀最热火的年代,夜攀族其实很低调,他们弄到房顶的不是马桶或女士内衣等不雅之物,而是倒扣的玻璃杯等只有知情者才看得出来的东西。此外,他们还千方百计保留作战记录,有个家伙攀墙时总是带着全套照相器材给同伴的勇猛无畏之举拍照留念,要知道,在笨重的大块头镁光灯相机年代,此举尤其彪悍。这些攀援行动都是玩真的,非常危险,带着一种异于现代人的精神气息。据一位圣约翰学院校友回忆,1952年某个凌晨他爬上吉尔伯特·斯高设计的礼拜堂塔楼,为第二天即将参加的学位考试打气。如今学生们备考恐怕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克莱尔石桥和其他故事
克莱尔学院有两则故事都牵涉到剑河上最古老的那座桥。桥上的石球不能算14个,因为国土学院那头倒数第二个球缺了一瓣。据说17世纪30年代晚期建造该桥的石匠托马斯·格鲁布故意让球缺一瓣,以抗议学院短他工钱的行径。不过有一个更说得通的解释,说这个角是为了偶尔检修球内与桥体相连的金属线而特设的,只是松掉了而已。近来,克莱尔学院有个学生铸了个很轻的真球尺寸仿制品,拿到桥上,等一艘载满游客的小艇划过来,就佯装癫狂状,“使劲”把球从桥栏杆往下“掰”,一船游客眼看球掰下了,纷纷跳进剑河逃命。这场天真无邪的笑剧让这位同学被校方停课受罚。
还有一个与水有关的故事。诗人托马斯·格雷担任彼得学院院士时,住在学院礼拜堂和圣玛利亚小教堂之间巴若楼顶层房间里,他人缘一般,怕火怕得尽人皆知,学生们便利用他这个弱点,在他窗口下面放了一大桶冷水,然后高声喊嚷“着火了”。格雷慌忙顺着一根绳子从窗口滑下来,一下子跌到水桶里。
恶作剧或者夜攀风潮都是学生圈子的事儿,和剑桥镇没什么交集,镇校双方最经常共享的是打架斗殴,尤其在过去几个世纪,如今偶尔也会复发。
2005年夏,剑河岸边卖冰淇淋的和招徕游客划船的导游两帮人大打出手。卖冰淇淋的是剑桥本地居民,一帮意大利移民;招徕游客的导游多是剑桥大学出来赚外快的学生。《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主打稿专门议论此事,新闻标题叫做“冰淇淋战争”。
死尸
医学教育居然也为学生提供了搞事机会。直到16世纪,医学研究基本都是照着课本纸上谈兵的理论探讨。1557年,奇斯医生在冈维尔学堂演示了人类尸体解剖,这在剑桥大学是第一次。1716年,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建造了第一间解剖演示厅。
剑桥大学曾发生一桩非常惊悚的“死尸”事件,18世纪30年代耶稣学院著名校友劳伦斯·斯特恩竟落到王后巷的停尸桌上。斯特恩虽然是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却入了教会。他凭小说《崔斯特·杉迪的生平和见解》出了名,这本书流传到后世,颇受伏尔泰赞赏。1768年,斯特恩因肺痨死在伦敦大理石拱门附近,尸体被葬在一个盗墓贼猖獗的墓地,果不其然消失了。没过多久,他的尸骸竟在剑桥大学解剖台上被认了出来,匆匆忙忙重新掩埋。《劳伦斯·斯特恩与死神》这幅画绘制于斯特恩去世后不久,如今挂在耶稣学院五百周年纪念图书馆的楼梯旁。
酒馆
酒馆是镇校双方打交道闹事的另一个舞台。剑桥镇向来客栈酒馆密布,部分是由于繁荣的河运网络生意。剑河及其大大小小的支流上,众多渡船主兼卖啤酒赚外快,许多剑桥酒馆的名称由此而来,比如铁锚、快乐水手和水岸等。
国王街怎么说都是小街一条,酒馆却曾经多达13家。这个了不起的数字催生了国王街豪饮赛,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国王街每家酒馆喝下一品脱杯啤酒而中途不如厕。以前学生们喜欢这么玩,如今游戏主要参与者是当地居民。哪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酒馆也火暴,往往蔓延到码头边,从教堂到莫德林学院之间短短的桥街就多达31家。
剑桥酒馆也走进了英国文学。耶稣巷和桥街交叉口的圆圈旅舍被威廉·华兹华斯写进了自传诗《序曲》。华兹华斯捕捉到学生初次来到剑桥的兴奋情绪,虽然他自己的剑桥生活并非人生最得意时期:
从山脚下驶过,继续前行
跨越莫德林桥,看到剑河
那著名旅舍“圆圈”亮了灯
我精神一振,心中涌起憧憬
(摘自《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9月版,定价:42.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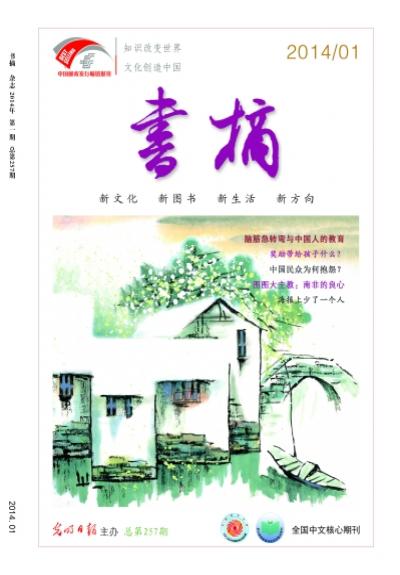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