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村,一个太行山腹地的普通小村落。
如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无数村庄一样,许村有自己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俗。但与同在山西的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相比,其在主流话语中,远不具备“古城”、“名村”的“历史文化价值”。
但当和顺县前政协主席范乃文带着这位当代艺术家到了偏远的许村,渠岩却意外地遇见了“失落的家园和故乡”。在自己有着千年文脉的家乡徐州早已“找不到一栋老房子”的今天,渠岩敏锐而惊喜地看到了许村尚保留完好的古朴与传统。坚定而坚硬的批判背后,更加深层的痛楚与柔情开始流淌。幸运的是,渠岩得到了范乃文这样的当地精英的支持,开始投入到对许村这样一个普通村落的价值发掘和重建中。
凤凰形的古村落
渠岩发现,这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村,其单体建筑并不具有文物级别的“价值”,但可贵的是其建筑历史线索的完整性。从集中于老村的明代建筑、清代建筑、民国建筑,到位于老村东南方向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建筑。从传统的“三裹五”、“五福临门”、“前商后住”的四合院,再到今天农民们新盖的院落。由于历史变迁,许多建筑都同时具有几个时代的特征,拥有历史各个时期的印记,在今天继续使用,显示了鲜活的生命力。
但是,当渠岩第一次来到村庄时,当地人对自己村落的历史和价值同样无暇顾及,和所有村庄一样,他们忙着外出打工赚钱,忙着用现代的吊顶和马赛克,装饰着城里人喜欢的“农家乐”。而彼时的渠岩,正在创作自己极富批判性的乡村摄影作品“权力空间”。
渠岩找来了他的好朋友,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的建筑师孟建民,成立了项目小组,希望通过梳理历史,来探索许村未来的规划方向。孟建民带领他的研究生,通过查阅县志、档案材料和老人的口述,细细地还原了村庄的历史。许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隋朝开皇年间,于、杨、范、王四家大姓迁至山下,在许村挖出了太行山区至今最深的老井。因此,全村最早的聚落形态是围绕老井而展开,直到今天,老井依旧是村里的主要水源。许村最早的村落形态是凤凰形,以古井和全神庙为中心,形成了“南文昌、北后土、中全身”的村落轴线,而在东西向上,则形成了以商贸车马道路为横轴的“明清商业街”。解放后许村成为乡镇所在地,在村子的东南方新建了人民公社、粮仓、小学等中心建筑。随着人口快速扩张,上世纪80年代后村庄扩建,逐渐突破了原有的凤凰形村落。
在许村的传统建筑中,运用了当地漂亮的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形成了丰富的堆砌手法。除了村落空间与建筑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外,许村的传统民俗活动尚保留完好。在传统节庆、祭祀和婚丧嫁娶等活动中,村民有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唱顶缸、唱晋戏等传统表演,还有剪纸、泥塑、木雕和木板刻画等手工艺传承。在传统信仰中,以对土地神的祭拜最为突出。在传统的院落中,每家每户都在进门的影壁处供有土地神龛。当渠岩将梳理后的村落历史展现给村干部时,他们又吃惊又感动。村民们对自己村庄历史的“无意识”,与他们对固有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对城市文化的向往是相关的。要想让村民认可自己的历史,需要逐步回归的,是他们的家园自信。
家园自信的回归
当渠岩发现了珍宝似的散落于山脉中的许村时,他也立刻注意到了村里一排排刺眼的新房子和美丽的河水边布满了整个河床的垃圾。虽然新村中的建筑依旧采用四合院的形式,但其排布已经没有了传统四合院依山而建的自然层次,而是沿着道路整齐地规划;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也不再是传统的红砂岩,而使用了流行的红砖材料。进门的影壁上的土地神龛,也被“福禄寿”所替代。有的家庭为了建新房,原地拆掉了老房,甚至变卖了老家具,让渠岩痛心不已。但村民们也无法理解渠岩对老房子的执著,在他们看来,生活改善了,孩子结婚了,自然是要住新房的。村里的卫生状况也十分糟糕,村民习惯于随手扔垃圾,没有人清理。渠岩为此找到村干部,但村干部们表示,如果没有上面的经费拨款,他们就没法做事。对此渠岩除了继续劝说村干部,只能是自己看到垃圾就捡,捡得多了,村民们感动或羞愧,也会跟着捡些。
和捡垃圾一样,既然无法在口头上劝说居民停止对老建筑的拆除,渠岩决心自己动手修复一栋老建筑,希望借此告诉村民,新生活并不会和老房子有矛盾之处。利用《大山的儿子》剧组在村里留下的几个传统建筑样式影棚,渠岩投入了改造。这就形成了后来的许村国际艺术公社,以及周围的乡村酒吧、艺术图书馆和新媒体中心等。此外,渠岩在北京收了两大车老家具贩子们从乡村低价收购来的老家具,带回了许村,带着村民,一起将这些老家具布置进了艺术酒吧和餐厅。
许村艺术公社的改造、“老家具还家”的活动,让村民们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老建筑改造的过程、改造后呈现出的效果以及自己那些“老古董”的妙处。渠岩带着村民参观艺术公社,一起布置老家具,希望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让他们理解老建筑的修复。一个村民感慨, “没想到老房子改造改造也能变成像国外的别墅一样”。渠岩对“老宅”的执著并不是盲目的怀旧和复古。在他看来,西方人的价值原点是灵魂不朽,因而可以用宗教约束其行为和道德。而古老的中国文明的价值原点是基于生命崇拜的血脉永生,体现在传统乡村社会,就是对祖宗的敬拜。人们在老宅的空间中祭拜祖宗,正如同西方人在教堂中祈祷忏悔。而修复老宅的背后,正是让传统家族伦理回归的愿景和信念。因此,修复老宅并不是修复它的文物价值,而是修复它的文明价值。
艺术节
在国际艺术界,艺术家们喜欢到有文化遗产的小镇或村落中度假和交流。许村自然风光优美,夏季凉爽,是避暑胜地,又相对更多地保存了传统文化,正符合举办国际艺术节的要求。2011年7月,第一届中国和顺·乡村国际艺术节开幕,对此渠岩说道,“我动用了我一生的资源”。
艺术节邀请了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在许村进行了近二十天的交流和创作活动,为这个古老的村子带来了惊喜和活力。前来参加艺术节的英国皇家美院前院长Paul在平遥古城住了一个晚上,就对渠岩说,回我们的许村去吧。一位澳洲艺术家,看到了这座与太行山自然共融的村庄时,大呼中国太神奇了。来自纽约的抽象画家大胡子Dickson说,在许村他看到了中国不为西方所知的一面。
许村的幸运或许正来自于它的普通,外国艺术家爱上了许村,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最意外却最在情理之中的中国。澳洲的艺术家Jason,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来到许村,他立刻爱上了这里。2012年11月,他自费返回中国,打算开始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创作,并且要在许村进行乡村儿童艺术教育的公益活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许村计划”在他看来最大的意义,是寻找到了保存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平衡,渠岩和艺术家们的努力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活力,让我们不至于在现代生活中迷失自己。而对于参加艺术节的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这同样是一趟反思和回到自己文化本源的旅程。
在许村,除了当年侵略的日本人外,这个村庄几乎没有来过外国人。在艺术节开办前,县里终于拨出了经费,整治了垃圾,添置了公共垃圾箱等设施。渠岩亲自写了一份文明手册,发放给每位村民,告诉他们一些基本的礼貌用语和文明行为。渠岩和许村,以主人的心态,认真准备着迎接宾客的到来。在20天的时间里,外国艺术家和村民的互动如何?没有在现场的我们难以用细节去例证。但渠岩说,外国艺术家的节俭和环保意识给了村民很大的触动。艺术节结束后,村里卫生环境的保持也比以往好得多。
许村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那天晚上,古老的村庄迎来了许久不曾有过的活力。农民自发地组织了舞龙舞狮、凤台小调等表演,来表达感激和快乐的心情。艺术节筹办的过程中,许村外出的年轻人纷纷回来,担任志愿者,或者经营民宿。艺术节结束后,艺术家每人留下了两幅作品,放在用空置的粮仓改成的乡村美术馆里。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让许村人极大地回归了对自己村庄的自信。面对央视《见证》栏目的镜头,许村的村干部说,以后村里年轻人找对象就好找了!
精神返乡路
追问渠岩这五年,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精力保护和修复许村是为什么,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是中国第一批当代艺术家。1992年起渠岩到捷克布拉格美术学院访学与教课,在与东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感受到独立知识分子在变革过程中的强大力量,这对他影响至深。在他看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底线,拥有独立的人格,为自己的每一次出场负责。然而,东欧的经历更加加深了他的孤独感。正是因为没有在自己的文化里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我像无家可归的孤儿,我在西方就像一个孤魂野鬼”。回国之后,面对快速现代化的城市和乡村,他发现,“我回到家也找不到根了,千年的徐州已经没有了一栋老房子,我已经没有了家乡”。所以当他遇见许村,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精神家园。
渠岩认为,要创造新文化,要带动经济,又不破坏乡村文化的肌理,需要一个当地的精英、艺术家、建筑师与社会学家等共同组成的团队,因地制宜地去制定村落修复的计划。而修复的过程,应该是类似于吴良镛先生对北京旧城改造提出的“小规模、微循环、渐进式”的方式,保持自然的更新。
借助在许村的实践,2011年的乡村国际艺术节提出了以抢救和保护老村为目的的《许村宣言》,呼吁停止目前对古村落的破坏,进行详细的村落普查,建立档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乡村修复计划”:在尊重传统营造法式的前提下,用当代的技术手法修复传统民居和民宅,在收集和整理传统的手工艺的基础上,找出与今天的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加以发挥和推广。复兴丰富的节日与仪式,融入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习惯,建立起来一个全新和完整的活动空间系统与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恢复一个有精神灵性、有伦理规范、彼此关怀和仁德本性的现代中国乡村。
(摘自《碧山02:去国还乡》,金城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4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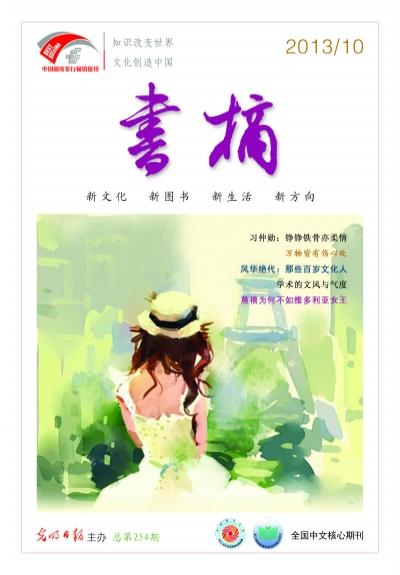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