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欧洲大学讲过学,外国人看到我一张东方人的脸,尤其我任教的叫东亚系,都会先问我从哪里来。我都会直接答以台湾,他们后来也都以台湾人在背后叫我。这个名称加在我的头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确实是在台湾住了一生,交游虽然从未限于地理环境,但所交大多数也是本地人,我很赞同周作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的籍贯与出生地都不是台湾,但把台湾认作是故乡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最近十几年,我的“故乡”认同发生了问题。很多人因我的籍贯是浙江,便把我看成大陆人,这一点我不否认,我的籍贯确实不在台湾,又因为我出身大学中文系,看人误会了中华文化,会把我以为正确的意见告诉他,久了后便有一部分人不接受我认同台湾,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而且语气很是不好,这让我忿忿不平,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呀。后来政府看到有些人在挑拨族群议题,便把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取消,代之以“出生地”。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台湾,都可以摆脱籍贯的困扰,做个名正言顺的台湾人了,但我不成,我只不过从一个外省转成另一个外省罢了,算来算去都是一个“中国人”。在此刻的台湾被称做“中国人”,不见得被敌视,但确实是被“异视”的,尽管我不论到浙江或湖南,手中都还得拿着大陆政府发的“台胞证”。
我其实不是那么在乎,我父母都是中国人,我当然也是中国人,我觉得我比一般人了解更多的中国,掌握到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中华文化精义,我以做中国人为荣。然而我自己做中国人,却从不“鄙夷”外国人,也从不轻视别人的文化。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可爱之处,不同文化也各有其价值。只是我已习惯了中国文化的节奏与气味,吃惯了中国的食物,习惯了用中国的文字与语言来表达我的爱与思想。这辈子我已别无所图,还是让我安安稳稳地做个中国人好了。
我们如果把中国做比较广义的解释,没有台湾人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来自中国。除此之外,我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台湾,甚至对中国的感情也是来自台湾,除掉台湾,我的中国是不完整的。所以中国对我而言是不能割舍的,而台湾也是不能割舍的,这不像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中国与台湾在我身上不是矛盾而是统一,不是排斥而是融合,二者是完全可以得兼的,而且除了少数政客,在这岛上,两者也得兼又融合得那么普遍。
我从没“回去”过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地。我到过很多次大陆,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最北到了松花江流入黑龙江的一个名叫街津口的地方。那是大陆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居住地,那里比“北大荒”更北。我们乘船在黑龙江上走,船夫得小心不越过江的中线,一过去就是俄罗斯了。最南面我到过海南岛的三亚湾榆林港,三亚湾最南的沙滩上有几块延伸到海的礁石,上面被古时的迁客骚人刻着“天涯”、“海角”的字样,每笔都透着绝望的心情,那是传统中国人所能到达的最南的地方。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而浙江鄞县,那个登记在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对我只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为什么没去过“故乡”?我一下子想不出明白的答案,也许是情怯,也许是因为自觉慎重所以要等待吧。我当然知道,大陆有些地方已彻底改头换面。譬如鄞县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鄞县现在只是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区,用大陆现在的标准,我算是宁波人才对。我对故乡的了解,全从古书中得来。古时候宁波是一个“府”,明清时府下辖有五县,即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国语》上说:“勾践之地,东至于鄞。”可见这地名在孔子之前就有了。然而这些历史上的故实,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宁波出现过一些名人,包括明清时期的屠赤水、全谢山,范氏的“天一阁”与“浙东学术”,民国时代的蒋家,还有包玉刚、董浩云等等,也都与我无甚关连。跟我扯上关连的是政府要人民登记户口出身,鄞县被有点莫名其妙登记上我的身份证,成为我的“籍贯”了。
我对父亲的事所知甚少,不知道他是否出生在他自己的家乡,对故乡的风物了解多少。也许他很早就离开了,对历史地理所知有限,他跟上一代一般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以飘泊“为业”的,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因为父母都去世得早,使我跟籍贯上的故乡没有联系的管道,不论父母,在他们的故乡应该都有“根”可寻的,但他们没有为我留下任何线索。所以所谓籍贯,都是由父母留下的一点文字上的符号,对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可言。
后来我知道了,我算浙江鄞县人不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报户口的时候我父亲已死,家人就以我母亲的籍贯报我们的籍贯。民法上有“从父”或“从母”的规定,我的姓是从父而来,而籍贯却是从母而来。这鄞县两个字跟着我一辈子,以前所有的证明文件,包括结业证书、毕业证书、退伍令、结婚证书甚至学校人事处印的教职员通讯簿上面都要登载的。
我没到政府机关去更改籍贯,一方面没这必要,一方面隔了一阵,身份证上的籍贯栏已去除,就更无须更正了。
我现在想谈谈我真正出生的地方辰溪,对这个地方,我其实同样模糊。抗战的时候,政府把重要的兵工设备搬到偏僻的山区,辰溪是湘西的一个山城。只记得小时候母亲哄我,常说不乖的话要把我丢给老虎吃掉。那是一个山岳溪谷纵横的地方,是不是还有老虎不得而知,晚上常听到凄厉的叫声,也许是野猫或是其他猛兽吧,野猫也会偷袭婴孩的。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沈从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几篇写的都是辰溪,那些故事我觉得都写得很好。由于是写我出生的地方,我便特别注意。有一篇名叫《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发生在辰溪的故事。沈从文写辰溪的时候都会把溪字写成谿,这两字是可以通用的,他写道:
辰谿县的位置,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河水深到三丈尚清可见底。河面长年来往着湘黔边境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山头为石灰岩,无论晴雨,皆可见到烧石灰人窑上飘扬的青烟与白烟。房屋多黑瓦白墙,接瓦连椽紧密如精巧图案。对河与小山城成犄角,上游为一个三角形小阜,阜上有修船造船的干坞与宽坪。位在下游一点,则为一个三角形黑色石蛆,濒河拔峰,山脚一面接受了沅水急流的冲刷,一面受麻阳河长流的淘洗,岩石皆玲珑透空。山半有个壮丽辉煌的庙宇,庙宇外岩石间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浮雕石佛。太平无事的日子,每逢佳节良辰,当地驻防长官、县知事、小乡绅及商会主席,便乘小船过渡到那个庙宇里饮酒赋诗。在那个悬岩半空的庙里,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听下行船摇橹人唱歌。街市尽头下游便是一个长潭,名斤丝潭。两岸皆五色石壁,矗立如屏障一般。长潭中日夜皆有五十只以上打鱼船,载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浮在河面取鱼。小船渑流而渡,艰难处与美丽处实在可以平分。
这是极好的描写文字,而文中所描写的正是我出生的地方。照沈从文的写法,辰溪该是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不料那儿好像没出什么人物,却是土匪强盗的集散地。他的这篇小说《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就是描写一个煤矿工人造反成了土匪头的故事。小说里面一个煤矿工人杀了一个兵,又抢了他的枪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就成了土匪头子。后来这个强盗被埋伏的官军捉到了,也就心甘情愿地乖乖就擒,虽然到死都还耍了些手段,却也死得痛快。这强盗做任何事,好像都气定神闲又安时处顺的,即使是死了,也让任何一方都不觉遗憾。我喜欢沈从文对人物的描写,也喜欢他描写的那个洪荒单纯的草莽世界。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辰溪这个盗贼出没的地方做故乡,也不想选择浙江。浙江比起湘西来,文明荟萃得多了,聪明又会打扮自己,我喜欢简单,我认为洪荒也许不够精细,但比文明要多一种粗犷的美,也比文明简单又有力,而且有力得多。不料我在辰溪只待了三年多,在辰溪的时候我根本还不懂事,父亲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死了。我约略记得,父亲的丧事办得很潦草,似乎找了隔山的一块地就匆匆埋了,墓碑是木制的,只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当然那种碑与坟,隔不久就会消失不见的。辰溪是我父亲的埋骨之处,我一度想回去祭扫,但浅浅的坟与木制的碑,还能祭扫得着吗?我再也没回过辰溪。
(摘自《家族合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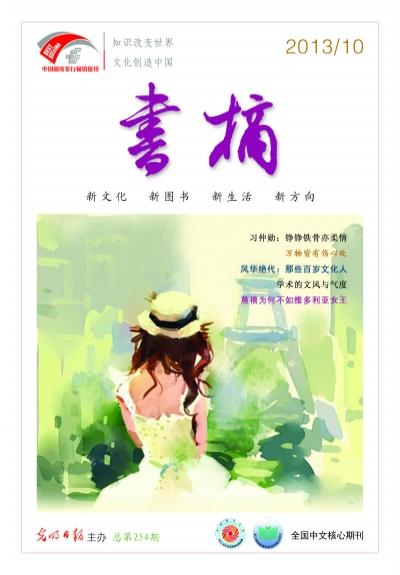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