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张申府先生接受了我这个西方人的访问。第一次会面是在11月12日,由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官员安排,在国家图书馆会客厅见面。1979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我那时正研究五四运动。在随后的五年中,我有幸成为张的对谈者。我们在他北京王府仓胡同的家中谈了总共七十多个小时。我们两人喝着茶,用中文交谈,没有第三者,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录音机。我一面听着他的生命的故事,一面发展我们的友谊。
对历史的回应
1980年6月16日。今天是我离华前最后一次探访张申府。我在他的好朋友李健生(章伯钧的遗孀)陪伴下谈了两小时。章伯钧是张申府的老政治伙伴,但迄今仍未恢复名誉。
今天张和李回忆他们政治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检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们不时发出自我挖苦的笑声,使脸上的皱纹更为显现。李:“真是的,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不能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革命在这一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
张申府望一望她,又望一望我,无可奈何地笑一笑:“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你可以说我们对社会责任放弃不了。但那时参与政治我认为是对的;我今天仍然这样看。您、我、伯钧和其他人想找第三条出路,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出路。但我想历史上我们是失败了。”
张申府的声音低下去,变得遥远。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有点迷失。李和张两人都沉思他们过去的政治失意,房间突然令人尴尬地沉静起来。
1987年4月30日。张申府的一位旧学生,历史学家赵俪生来威斯里仁大学探访我。在远隔中国千里的大学宾馆里,赵把我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回到他在清华大学初上张申府逻辑课的日子:“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他也总是倾向中共这一边,即使他不是中共党员时也是如此。他不像梁漱溟,他没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头脑。”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我问这位71岁的老人,“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可否帮我从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的传统角度了解张申府呢?”
赵俪生停下来,仔细地望着我,然后尖笑起来:“您懂中国诗,您听过汉朝《弃妇》那一首诗吗?”
“我不大清楚你是指哪一首?”我说。
赵于是拿起笔,写下以下的诗句:
死亦无别语 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 犹得生君家
我表示看懂那些字,但却不明诗的意旨。
“这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赵继续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
政治与哲学
1981年6月11日。我和张申府进行了关于哲学和政治的谈话,张强调“政治一定不能够干涉哲学”。我对他挑战。我指出以下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你一生都和政治分不开,你经常用你的哲学肯定政治参与。1928年你写孙中山和逻辑,好像孙先生的说话是哲学家的说话。在抗日战争中,你写过无数的关于哲学和战争的文章,给人印象这二者是互相补充,自然而然的一样。”
张申府一时间停止说话,转头望向他处。停顿的时间不长,当他再回望我时,他的答案是简单的:“我仍然相信哲学不能被政治干涉;但哲学免不了影响政治,却是自然的事。”
1980年4月15日。今天我访问了冯友兰,张申府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的同事。他也是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走过非常艰辛的道路的人。这位八旬老人在30年代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对张申府很熟悉,因为是他聘请张在哲学系任教的,而且他也经常给张所编的“世界思潮”专栏投稿。
1936—1937年间,这两人的发展方向有了不同。冯友兰钻研他的儒家人文主义,成为人生哲学的主将,而张申府却走向辩证唯物论。1937年,张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旗手,对这冯友兰完全没有兴趣。今天冯告诉我为什么:“张申府先生的哲学观,和我的比较,一向是较为高昂的,又或者可以说是较为功利主义的。我的看法,一贯都是哲学只有有限的社会用途。在这方面,我和张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他总是相信,如果人们可以哲学地过生活,那生活就会好些。
“新启蒙运动是他大规模地宣传他的信念的方法。这个运动要启蒙广大群众,要把哲学带给广大群众,但我总感到这个运动有点自大。我有相反的看法。我相信有人的地方便有哲学。每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哲学家去训示他们。”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说张申府的自大,冯友兰的评论给我以另一观照。透过哲学界同仁的眼睛,张申府的哲学救世主义似乎是他个人气质和选择的结果,而非政治的需要。
最后的忏悔
1980年6月2日。今天我本打算和他谈1920年参加中共的事,但他却转而讲到刘清扬,最后并探讨他和刘于1948年分手的原因。张申府对他的风流往事以及对刘清扬自尊心的伤害想得越多,他就越觉愧悔:“我对她不公平。她自从在巴黎和我一起开始,就对我很迁就。……我和孙荪荃的事以及后来在重庆我和学生董桂生同居……我做了很多事使她愤怒……但如果我没有写1948年那篇文章,这些我们都可以解决。30年的感情,就因为这一愚蠢的举动毁诸一旦。”
“我一生后悔的事不多,但这1948年的文章(1948年10月23日《观察》杂志头版刊登了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是我后悔的事情之一。另一件事是1925年退出中共。我其实可以有其他不这么冲动的方法表达我的意见。想想,如果我不是被赶出革命的大门的话,我的命运会怎样?唉,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我总是不能够叫自己闭口,我总是不理后果,想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没有政治智慧,不懂得有时要睁一眼闭一眼。”
“是啊,这老头仍是很笨的。”几分钟前走进来的张的妻子关素文附和着。她通常在下午将完的时候参加我们的谈话,我转向关素文,预料她会如常一样供给我一些零星资料。
张申府哈哈大笑,说:“是的,我一向都不循规蹈矩,为什么现在要呢?”
最后的回答
1967年9月21日。在红卫兵监视之下,张申府整理他的供词:《我的教育、职业、活动》。这个1904—1967年的生平大事记,从题目到内容都不亢不卑,并不是一篇低头认错的文字。在适当的情况下,他还突出一下他在中共创建上的角色以及与一些党史歌颂的人物例如李大钊的亲密关系。他没有丑诋他的朋友例如陈独秀和梁漱溟。他简简单单地、实事求是地叙述他怎样在1921年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以及怎样在1948年写出《呼吁和平》这篇文章。
1949年之后的部分,较多的自我批判。到1965年,“若有若无”地供道:
我对于毛主席的著作不是不重视,不是不珍视,也不是不学习不读。只是重视珍视,而不熟读。即或也学习也读,而并不真懂,读了也不用。这次又重读了以后,自觉直到这年10月才算学习入了门,才懂得了一些主席著作的真意义、真价值、真精神,才感觉到主席的句句话都是真理、是阳光、是空气。
到最后结论时,他意图把他描述章伯钧的话,套在自己身上:“我是百分之九十五站得稳”:
自5月中旬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外单位或外地来访问,了解“一二·九”运动时期的旧人旧事。因为那次运动我是北京的出面负责人,许多参加的人都是我的学生或同事,而这些人,据说今日许多已成了高中级干部。凡是问我的,我无不竭诚如实,尽所知所能记忆的以告……一位同志对我说,你讲的情况最多,记忆力也最好。
自从1979年平反后,张申府成为修正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张申府是中共革命伟人重新定位的关键人物。
1987年2月9日。张申府逝世后一年,他的政治地位的恢复达到高峰。民革的报纸《团结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文章,几乎全部引自张的自述。此文的内容和张于“文革”时在红卫兵迫压下的交代,可称无所分别,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语调:现在这语调是处处维护,处处赞扬。
张申府从一个已被遗忘的中共党小组的创建人,一变而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史的一个主要见证人,这表示张的正式平反已差不多完成了。但官方平反不等于自我平反;张申府过去十年所追寻的,是自我平反——他与我的谈话,目的正在这里。
在他的心目中,他首先确定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这也是他自傲的所在。然而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要坚持作为一个思想家,是不容易的。虽然搞政治的人早已对思想没有兴趣了。张仍没有放弃这个追求。
1980年4月14日。他谈到他的哲学:“您知道,过去几个月我尝试总结我的哲学立场。您的谈话刺激了我,使我想到一些新问题。我现在开始写我的哲学看法,或者叫《我的人生观》什么的。我曾经分析我的人生角度,客观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弱点和成绩。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观的演变,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
“我想我最后得出了三个字,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实、活、中。”
张申府接着满足地捂着嘴笑起来,仿佛发掘到了一个宝藏。他一向喜欢把思想浓缩为几个字,这旧癖好又再故态复萌。他拿起我的笔记簿,“看,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字写给您。‘实’,您知道,是我在‘五四’时期开始时一篇文章的中心信念。我常写文讨论真实的重要,及人们对真实视而不见的偏向。我的大客观哲学,目标就是求实。
“‘活’,这个字看去多么简单,令人想起生活。但我的意思比较深入,比较接近辩证唯物论,它是关于事物常变,我们需要经常适应配合。这不同过去所宣扬的死硬教条,这不是真正的或活的马克思主义。
“‘中’,就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对我来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另一轮的极端主义,正在恢复,因此特别需要真正了解什么是中道,以及它现在的意义。”
谈话结束后,张申府手里拿着一份稿件: “这是给您的,《我的人生观》的暂定稿。”
我看着这七页满是手写字迹的稿纸,又是感激,又是奇怪。张在抱恙之中,竟然亲手给我誊写了一篇稿件。这是他今年春天的思考成果,文稿的字迹笔划有些不稳,但仍然清晰可读,证明他是花了很大气力抄写的。我对他这份礼物表示感谢。
1982年7月。张申府的哲学宣言最后付印了。两年前张给我看的初稿题目是:《我的世界观——漫谈如何为人(怎样做人?怎样对人?)》现在印出来的文章没有这些副题,干脆就是《实、活、中》。
文中还有一些和原稿不同的地方,张申府的马克思乌托邦思想被降了调。虽然有这些修改,张的思想仍然被忠实地保存下来。我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这老人试图总结他的一生,并告诫同时代的人。他这一生坚执己见,高傲自信,付出的代价可说甚大。但他这一生也是对个人的信仰操守从不失去信心的一生。
张在结论时以诗歌般的文字赞颂他的三条信仰支柱:
知息息不息,易易不易。快乐太快,至乐不至。人生至乐,乃在从从容容地对实、活、中的真知、实践。
透过《实、活、中》这篇文章,张申府成功地在他自己心目中平反了。自从他1979年得到官方的政治平反后,他所做的和他所写的一切,都不及他这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了他的哲学总结并予以发表这样使他高兴。
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相信这篇文章是张申府悠长的生命最恰当的墓志铭:“易易不易……人生至乐,乃在从从容容地对实、活、中的真知、实践。”
(摘自《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定价: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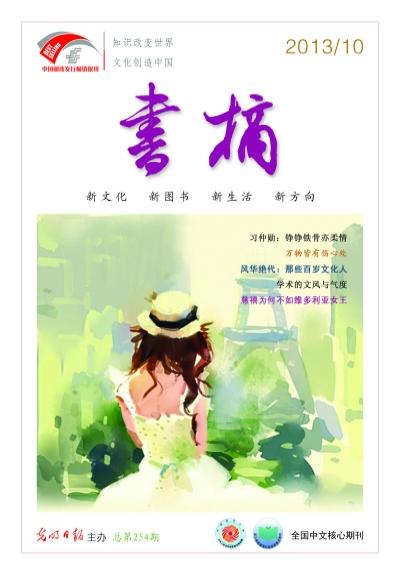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