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针外交的由来:蛇的故事
以胸针作为外交工具的想法在国务院的工作手册或者任何记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文字中都无迹可寻。事实是如果没有萨达姆·侯赛因,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一切了。
在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总统任期(1993—1997)内,我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时值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击退了伊拉克对邻国科威特的入侵。作为战后协议的一部分,联合国要求伊拉克接受其核查,并提供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项目的所有内容。
当萨达姆·侯赛因拒绝合作时,我竟敢批评了他。于是由政府控制的伊拉克新闻界便发表了一首题为“致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没有问候”的诗。作者在诗歌一开始便定下了调子:“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得了吧你,得了吧你,你是这个暗夜里最丑恶的东西。”接着又勾画出一幅抓人眼球的视觉图像:“奥尔布赖特,没有人能阻挡通往耶路撒冷的大路,哪怕是用驱逐舰、鬼魂或是大象。”至此热度已完全煽起来了,诗人便说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噪音制造者”,“一条绝无仅有的蛇”。
1994年10月,此诗发表后不久,我要如约会见伊拉克官员,戴什么呢?
几年前,我曾买过一枚蛇形胸针。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因为我向来讨厌蛇。然而,当在华盛顿一家我最喜欢的店铺里看到这枚蛇形胸针时,我却无法拒绝它的诱惑。胸针很小,是一条盘绕在树枝上,嘴里吊挂着一粒小钻石的蛇。
在准备会见伊拉克人的过程中,我想起了那枚胸针,决定就戴它了。我并不认为这一举动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怀疑伊拉克人是否会联想到那首诗。然而,会见结束后,遇见一位联合国记者团的成员,她熟悉此诗,便问我为什么要选择戴那枚胸针。所有的电视摄像机聚焦在我的胸针上,我笑了笑,说这不过是我传递信息的方式而已。
没过多久,我猛然发现,不经意间珠宝已经成为了我个人外交武库中的一部分。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曾以“读我唇形便知我意”闻名,于是我开始恳请同事和记者们“读我的胸针”。
由于我的前任们都是留胡子、没有一个穿裙子的,我这种利用胸针来传递信息的做法便在美国外交中显得十分新鲜。
胸针与勋章的较量
我喜欢服饰珠宝的一个原因是它既养眼,又不会掏空你的腰包。现代女性应该在打扮上大胆试验,尝试不同的想法。以我的身高(5英尺2英寸),我一直都以为小型胸针对我来说最合适,但不久后我便开始购买更大、更醒目,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类型。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的是那种大胆而非娴静的打扮。
鉴于我的胸针变得越来越富有表现力,并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议论,我认为很有必要对外表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深入思考。把“衣服成就女人”那句老话改一改,胸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一个女人,或者就此而言,成就一个男人?毕竟,胸针的展示从未局限于某一性别。中世纪的骑士就通过佩戴镶嵌有精美珠宝的徽章来标明其地位和表达群体认同感。
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全专家依靠密码胸针来识别那些可以进入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使之与那些不能进入的人区分开来。人们会发给国会议员胸针,以避免在去往办公室或立法楼时被警卫拦下。俱乐部和秘密会所通常会使用徽章(再加上神秘的握手方式)使内部成员能识别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
我们的军队也同样利用胸针——以绶带和奖章的方式——来传达与成就、名望和军衔有关的信息。我是在出任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注意到这一点的。
199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科林·鲍威尔将军。我们都是克林顿国家安全小组的成员,并面对面坐在白宫形势研究室那张长长的条形桌旁。尽管我们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看法一致,却在美国和北约是否应该介入,以制止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境内的波斯尼亚发生的种族清洗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并列举了应该这么做的理由;鲍威尔将军则表示怀疑,也列举了不应该这么做的理由。我的窘境是尽管我佩戴着表示爱国精神的胸针,他的胸前却挂满了当之无愧的军功章;他刚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中归来,穿着军服,自信潇洒;我却刚从乔治敦大学的教室里走来,而且,即便是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看起来也像只粽子似的(那是在我开始健身前)。
但我也深知大家让我在形势研究室内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要我像棵盆栽植物似的一言不发。我打断了他,说美国迫切需要制止在巴尔干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鲍威尔则用教鞭和幻灯,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预期:此次行动弊将远远大于利。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陷入了僵持局面,政府也未采取任何行动。随着屠杀的继续,我变得十分沮丧,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让压抑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科林,”我问,“如果我们有这么一支优秀的军队却不用,那留着它又有何益?”在他的自传里,鲍威尔写到我的这个问题几乎让他喷血,他不得不跟我解释——耐心地——美国武装力量应起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愿意承认将军小心谨慎没有错,提出质疑没有错,考虑别的解决办法没有错,担心平民领袖的浅显假设没有错,然而,我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却是正确的。后来北约最终介入,并由此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
胸针的寓意
1997年初出任国务卿后,我对胸针的嗜好开始变得广为人知。《新闻周刊》封面上我那张把山姆大叔的大礼帽与鹰合戴的照片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我佩戴胸针拍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公众对之产生的联想也随之增加。时间越来越不够用,我去商店闲逛的机会也减少了,但没关系,因为大家开始送我胸针了。
外交人员初次会面时,只有互换礼品才会被认为是文明人。从法律上来说,美国官员可以保留低于某一价位的外国礼品——在我那个年代,是245美元。超过这一价位的贵重礼品就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可以拿来展览,保存,或者出售,所得收归国库。另一个选择就是全价买下礼品,我有几次就是这样。有些特别巨大的礼品,比如蒙古国赠送的活蹦乱跳的骏马,或者马里赠送的咩咩直叫的山羊,实际上是由主人留了下来。我怀疑,它们曾不止一次地被赠送给经过乌兰巴托或者巴马科的政要。
给一位外长选一份完美礼物就如同给一名远房亲戚选一份“恰如其分的礼物”,作出选择需要集常识、直觉和猜测于一体。我赠送的礼品一般来说颇具美国特色:给男人,鹰袖扣;给女人,一枚特制的背后有我签名的鹰胸针。
《圣经》教导我们说给予要比接受有福,却没说哪一个更有趣。我在外交界的那些同事们于是很高兴地猜测,对我来说,一枚有巧思又不贵的胸针一定会受欢迎。他们猜对了。每当收到包装好的礼品盒,解开丝带时,我都怀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和珍爱。我碰到的唯一问题是一定要记得在下次与馈赠礼物的人会面时戴上被赠的胸针。
我最喜欢的礼物里有一份是莉亚·拉宾——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的遗孀——赠送的。胸针是只和平鸽,象征着总理为之献出生命的目标——“圣地”的和平。
1997年8月6日,我出现在国家新闻俱乐部里,概述了中东和谈要点,并宣布了将前往这一地区的计划。莉亚·拉宾是听众之一,她注意到了那枚显眼地别在我胸前的和平鸽胸针。
几个星期后,拉宾夫人来到我在以色列下榻的饭店探望,并带来了一条与胸针相配的项链,由一群和平鸽组成,还递给我一张便签,上面写道:“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一燕不成春,——所以也许一只和平鸽需要增援,才能在中东地区把和平变为现实。我们需要希望,而希望已经失去太多——我真的期待你能重燃希望。衷心地祝福你,莉亚。”
之后的三年里,我在中东投入的时间要比在其他任何地区都多,克林顿总统也是如此。尽管我时常佩戴和平鸽胸针,但对谈判的步履维艰不满意时,我也觉得有理由替之以海龟、蜗牛、(或者真把我惹恼的时候)螃蟹。让人难过的是,没有一枚胸针完成了交给它们的任务。今天,拉宾夫人那充满希望的表态已过去了很久,和平鸽却依然需要增援。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我的胸针,自然而然地,我发现自己变得刻意起来。早晨,甚至在前一天晚上,我就开始琢磨第二天戴什么胸针合适,有时甚至琢磨起每一次会议要戴什么。我没有多少时间准备海外之行,因此常常是从首饰盒里用手抓一大把,然后希望届时能从中找到合适的。有些胸针从本质上说就是心情的表达,以表明事情进行得顺利与否。感觉好时,我常常会戴枚瓢虫胸针,因为谁不爱瓢虫呢?第二个选择就是热气球,我自己的解释是它代表着高飞的希望,而不是过激的言辞。别的胸针则致力于表现某种使谈判得以成功所需要的品质,比如宁静的天鹅和智慧的猫头鹰。
由于我从本性上来说是个爱担心的乐观主义者(以区别于易满足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我发现佩戴自己那枚金光闪闪的太阳胸针的机会还挺多。当然,外交官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在难有可为的情况下尽力而为,所以我有时佩戴这枚太阳胸针更多的是表明希望,而非预期。
当然,不是每次外交会见都需要阳光般亲切和蔼的态度。每当要表达措辞激烈的观点时,我通常会戴一枚蜜蜂胸针。默罕默德·阿里过去常夸口说自己要“飞翔起来像蝴蝶,叮咬起来像蜜蜂”;而本人想传达的寓意是美国会尽力和平解决每场纠纷,但如果被逼无奈,我们有决心也有办法进行反击。
另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排列多个胸针。有些可以很自然地搭配起来,比如我与曼德拉会面时戴的斑马胸针,别的组合则需要更多想象力了——例如,蜜蜂如何靠近向日葵。试验各式各样的搭配方式挺有意思,但这样做会耗费太多精力,而且这还不包括下面这个现实问题:我的衣服被胸针穿得满是洞眼,简直就像接飞镖的底盘,最后只好戴更多甚至更大的胸针来遮掩破损的地方。
勿听坏话,勿出谗言,勿视邪恶
1999年春,当时北约各国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庆祝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克林顿总统与外交政策小组会面。我们刚坐下来办正事,摄影记者戴安娜·沃克尔却被允许走了进来。拍照对公关有益,却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停止谈论某些机密问题。为了生动地表达保密的必要性,总统用手捂住嘴,做起了怪相。接着国防部长比尔·科恩用双手捂住了耳朵。领会了他们二位的意思,我立即捂住了眼睛。我们简直就在照相机前耍起了宝,逼真地模仿起著名的“勿听坏话,勿出谗言,勿视邪恶”。
沃克尔拍摄这张照片时,我还没有三只猴子胸针,不过很快我就在布鲁塞尔找到了一套,每枚都以象牙坚果雕成,坐在凸圆形玻璃(粉红、紫色、橙色)底座上,环绕着一圈水晶。猴子作为警告诱惑的由来已湮没于日本民间传说的迷雾中而不可考,但这一劝诫至少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并与要为错误思想和行为承担责任有关。著名的Kikazaru(“不听”的猴子),Iwazaru(“不说”的猴子)和Mizaru(“不看”的猴子)至今还可以在日本日光市17世纪的东照宫神社的大门上方找到。
我第一次有机会佩戴猴子胸针出访是去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我打算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俄罗斯在车臣地区人权问题上麻木不仁的态度。俄罗斯军队有合法理由打击搞叛乱的恐怖分子,但出手太重,只会树敌更多。我提出应该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该地区以保护平民。普京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否认做过任何违犯人权的事。他对邪恶视而不见,一如我的胸针。
尽管我们在车臣问题上存在分歧,俄罗斯人却对我释放出的信号十分在意。普京曾对克林顿总统说他平常都会看看我戴什么胸针,并试图解开其中之意。有时我的选择会反映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升温,比如佩戴那枚金制太空飞船胸针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但更多时候,气氛是紧张的。普京,年轻有为而又自律甚严,取代了鲍里斯·叶利钦,而后者这两种品质都不具备。我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第一印象是复杂的——很显然他有才干,但他天性上似乎是专横多于民主。
在我们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就包括核武器问题。美国希望对反弹道导弹条约进行修改,我们的对手却不想。谈判开始时,俄罗斯外长看到了我为那天特地选戴的一枚形状似箭的胸针,便问 :“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我说:“是啊,你也看见了,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做得很小,所以你们最好准备谈判。”
关于导弹的争执证明了冷战的惯性思维消失得很慢。
(摘自《读我的胸针:一位外交官珠宝盒里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
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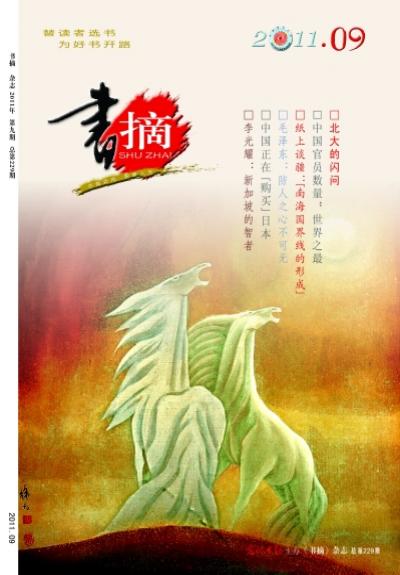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