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他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还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第一部 城墙
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53岁,长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儿,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
“这一带有33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
“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第二部 村庄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做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360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第三部 工厂
在浙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到温州之后没有多久,陶氏姐妹和任静都离开了这家工厂。看来,那也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在假期到来之前,他为拿到更多的薪水进行了艰难的协商。随即,一旦奖金和红包到手,他就把几个女孩儿撤了回来。她们几个回到了丽水,一起在一家生产烟灰缸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玉凤满16岁之后,就好在大公司找工作了,她们于是又跳槽到了华都仿皮厂,具体工作是质量控制。她们监测着成品,找出有瑕疵的产品。经过她们的批准之后,一卷一卷的仿皮被送到了世界各地。
我最后一次去丽水考察的时候,到陶家那个单间的棚屋停留了一会儿。玉凤刚刚下了班,一提起她的工作,她就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们要给加班工资哦!”她说,“我每个月发900元,如果把加班工资算进去,一般会有1500。”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是入门级流水线工人工资的一倍还多。玉凤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工厂生产的皮革质量不是一般地好:有的用来做摩托车坐垫,有的用来做汽车内饰。“我喜欢我们的老板,”她说,“如果我们做累了,睡着了,他也不会发火。如果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长了,他会给我们买水果、零食之类的。真好玩。”
她打算在仿皮厂再干上一年左右,然后用家里的积蓄做点生意,也许跟她爸爸一起做吧。他们想开一家正儿八经的商店——有屋顶有门窗的那种,而不是沿街摆放的小摊儿。
“在皮革厂你不能做得太久,”她说,“那儿有毒,对人有害。我们做质量控制的还好点,但也是对身体不好。你在那里呆上一两年,就要离开才行。如果不是因为有毒,在那个地方上班倒是很不错的。”
玉凤就要满17岁了。我第一次遇到她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她当时拿着姐姐的身份证第一次出来找工作。那个时候,她的个子有些矮胖,身材像个男孩子。她抓着胸罩调节环的架势,如同在把玩着赌博用的筹码。她说自己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此向老板推荐自己。然而,在20个月的时间里,她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编造的那个故事。她儿时的肥胖不见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美女——高高的颧骨,精致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发型。她修了指甲,这在打工妹中间是很罕见的。小村子已是两年前的事情,更是另外一个世纪的事情,她没再谈起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没有说起过原来的同班同学。她想要说的就是明天——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生活,以及随着时光匆匆流过,其他有望实现的所有事情。
(摘自《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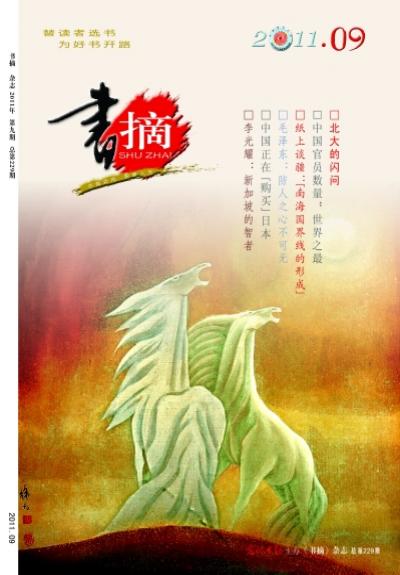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