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京城的时候,汤一介正在北大哲学系埋头读书,继续着他高中时的梦想——将来做一个哲学家。多年以后,渐通世事的他才明白,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时代,已经不可能像昆明那样“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安静的书桌、哲学家的梦想是奢侈的,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京城的时候,汤一介正在北大哲学系埋头读书,继续着他高中时的梦想——将来做一个哲学家。多年以后,渐通世事的他才明白,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时代,已经不可能像昆明那样“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安静的书桌、哲学家的梦想是奢侈的,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
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
马国川: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您在想什么?
汤一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梁效”受过一段批判,把我们集中起来做检查,搞了一年多。到1978年才把我们解放了。解放出来以后,开始让我们做资料工作,我们就编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做注解。当然做注解也有好处,要弄清楚那些话怎么讲。一直做到1980年,我自己觉得,我们得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感觉到1949年以后哲学研究上问题比较多。我们学习苏联的那一套东西,学习苏联的教科书的体系,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利于我们中国的健康发展。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考虑:原来的说法是,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我就想,能不能把哲学史看成人认识的发展史?既然是人的认识史的发展,不仅唯物主义会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唯心主义也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几乎是在我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有些老先生也发表了讨论哲学范畴的文章,比如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
马国川:大家试探着突破禁区。
汤一介:1981年,我就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这种课在1949年以后是很难开出来的。我开的这门课非常受欢迎,三次换教室,一次比一次大,最后没有办法,就发听课证上课,外面来听的人很多,当时周一良教授也来听,他可是研究魏晋史的专家。
马国川: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喜欢?
汤一介:因为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另一方面,那些教条主义的课程很冷淡,这说明,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更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还是很愿意听的。其他的课程都有这种情况。到1983年,著名的美国罗氏基金会给我资助去美国做研究,我就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我首先碰到杜维明先生他们这些现代新儒家。他在哈佛大学做教授。我原来不是研究儒学的,我是研究魏晋玄学也就是道家思想的,可是出去就碰到这些现代新儒家。
杜维明大概1979年已经来中国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也常来我家。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的思想并不了解。到了哈佛,发现他们都讲儒学,我想是不是应该了解他们的思想?现代新儒学这个路子是不是好?现代新儒学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非常大。但我当时觉得这个路子可能有一点问题。他实际上还是希望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里发掘出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当然不是说我们一点民主思想没有,但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别的角度考虑中国哲学的问题。正好那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会。我在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做了一个演讲,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我是从真善美这三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可以从三个基本命题发挥出来,一个是“天人合一”,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知行合一”,是解决人社会生活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景合一”,就是人的感情和外在的景物结合才可以产生美感的问题。我讲了以后大家热烈鼓掌,反映很好。台湾有一位学者给我提出问题,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怎么一句也没有提马克思主义呢?我一听,他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我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把他给顶回去了。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后面那一篇文章我把孔子和康德做了比较,老子和黑格尔做了比较,庄子和谢林做了比较。中西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哲学家都想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是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后来我考虑的问题又受余英时启发,余英时提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一个不同,西方哲学是以外在超越为特征,我们中国哲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不错,西方的外在超越是容易建立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国哲学讲心性之学,是靠个人的修养,也许在伦理道德方面有可贵的价值资源。
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马国川:您什么时候回国的?
汤一介:我待了半年多就回到国内了,那是1983年秋。乐黛云1981年就到哈佛燕京做访问学者,当时不让我们俩一起出国,怕两个人一起出去就不回来了。其实我们留在国外有几次机会。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研究中国的学者,必须在中国。像杨联陞先生如果在国内可能就糟蹋掉了,但国内的环境如果不是那么糟的话,他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他很难过,我跟他聊天,他有时是眼泪汪汪的。他说是跟着“老毛子”,为外国人在工作,老是围着人家的研究计划转,人家需要什么,他研究什么,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有鉴于此,我就回国了。
1984年暑假,我去夏威夷参加了一个比较哲学会议,从这个会上回来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年轻学者已经开始运作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了。他们都是哲学系的助教,包括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人。他们得到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支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都支持他们。我回来以后,他们就找我,他们就让我做院长,同时请冯友兰先生做名誉院长。办“中国文化书院”光靠北大教授也不行,那个时候梁漱溟先生还在世,所以我们就把梁先生请过来做我们学术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的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介绍海外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导师中各种各样思想的人都有,梁漱溟先生是坚持儒家之道的,反对儒学的包遵信也是我们文化书院的导师,还有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像我这种年龄的学者中比较倾向于传统文化的是庞朴,他现在还主张“中体西用”。杜维明是我们书院的导师,新道家,陈鼓应也是我们导师。我们内部确实思想不一致,我虽然不赞成新儒学,但是我不公开地反对它,我觉得应该“和而不同”。
从我个人讲,愿意继承蔡元培的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你各派都可以,包遵信可以参加,杜维明也可以参加,陈鼓应也可以,李泽厚也行,这都没问题。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原来教条主义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同时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搞“新启蒙”。
完整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马国川:在今天,您怎么来评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延续了好几年的“文化热”这种社会现象呢?
汤一介:大家觉得文化很重要。1985年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文化协调会议”,除了北京的学者外,还有上海的王元化、武汉的肖箑父、西安的陈俊民等等,清华大学的刘达也来了,同时也请了杜维明参加,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魏斐德。后来我们发表了一个纪要,认为中国只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除了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
马国川:政治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当时似乎有点犯忌。
汤一介:对,很犯忌,我们着重讲文化现代化。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真正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你不能只是一个方面的现代化。其实从清末就要搞什么现代化,每一次现代化被打断的原因之一,就是单纯考虑经济,没有考虑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断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建国后大讲特讲的现代化也被打断了,因为没有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相配合,光是经济现代化很可能会走弯路的。
马国川: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有人批评当时的“文化热”,比较浮躁。
汤一介:那是肯定的,本来是有点浮躁嘛。因为一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不能都很深刻,不能都很正确。90年代开始“国学热”也不一定都正确,包括现在的我们学术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我更不了解了。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
马国川:但是进入90年代,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90年代后期李泽厚有一个说法,认为80年代属于“有思想没学术”,90年代“有学术没思想”。上海王元化先生反对这个说法。
汤一介:要严格地讲,李泽厚当然不是很全面,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我们经过80年代,很多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因为太快了。
马国川: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80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80年代形成,但他90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学术也不太多,因为90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做学术,真正做学术的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但80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可是浮躁之风就是90年代开始的,主要是经济大潮把人弄坏了,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各个方面的问题。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没有著作就不能当教授,而且一本还不行,甚至两三本都不行,制度使得学术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马国川:90年代您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90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9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马国川: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对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的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马国川:那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就是中国的文化世纪”、“中国文化能救世界”等说法甚嚣尘上。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现在是互相影响,因为人类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时代。
马国川: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美国的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和人要和谐,人和人要和谐,情和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马国川:中国传统文化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斗争的哲学,即使在法家的韩非里面也只是一种权谋之类的东西。
汤一介:没有上升到哲学。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从1949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就是斗争哲学,所以搞得中国太苦了。
马国川:一方面批评“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文明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您是“两面作战”的状态。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上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能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马国川:今天的思想界也是很混乱的,您看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要搞国教,您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原来是政教合一的东西,后来走不下去了,必须政教分离。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他就会排斥异己。西方假如真正要坚持自由、民主的话,就不能政教合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就不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你提出来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看看从西方讲,从中国讲,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好呢还是坏呢?这个也可以讨论。
马国川:也有人说,我们这套传统文化挺好,这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什么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这里都有,这个东西就是西方的民主,甚至说就可以拿我们的东西来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不同文化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吸收人家的基础和能力。
我是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时代,你要多考虑人家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行,而且最好是不同文化之间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对方,不要封闭。
马国川: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思想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不能定为一尊。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怀疑的权利。政治上可以有指导思想,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如果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办法发展学术了。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马国川:作为一个哲学家,您认为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了思想家?
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说我是一个哲学史家可以。为什么呢?解放以后有一个问题:什么人才能做哲学家?就是马、恩、列、斯、毛才是哲学家,他们是创造思想的人,我们只是解释他们思想的人,或者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历史,我们只能叫哲学工作者,不能叫哲学家。所以,我就从来不说自己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
他们不让我们做独立思考,就只能按照他们的那个模式、框架来思考问题。
我觉得现在还谈不上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可以把各种思想整合起来的思想家,还没有到这个条件。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既有时代的问题,也有个人的问题。要比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老专家,国学基础和西学基础都不如他们:我父亲汤用彤和冯友兰那一代都是受过私塾训练的,然后到十几岁、二十岁出国了,在那儿又待了好多年,至少四五年,或五六年以上,所以对西方比我们了解。我们没有机会出国,两个基础都比较差。我们自己也是不努力,勤奋不够,但是主要的还是社会环境,我们没法学习,大部分时间耗在运动里面去了,写什么思想总结、检查,比写的书要多得多。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出去,都是短期,没有长期真正了解。解放以后,从哲学上比较有一点点创作的是李泽厚,其他就找不出太多人了。但是总体来看,建国后的学术思想著作都很难成为经典,不像30年代有些书,今天还不能不读它。所以我们这一代不大行,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好处,毕竟在刚解放的大学读过书,还知道一些东西。我们等而后之更不行了。
中国宋明的时候可以整合理学,西方哲学经过文艺复兴整合了西方思潮,中国现在可能还是过渡时期,大家来讨论吧,要慢慢做,但是不容易。现在要寄予希望的恐怕是“八〇后”、“九〇后”,甚至是“二十一世纪后”了。他们要国学基础好,要西学基础好,才有可能出现一些既有思想又有学术的大学者,因为30年代确实这样培养出了一大批人,像胡适他们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摘自《我与八十年代》,三联书店2011年6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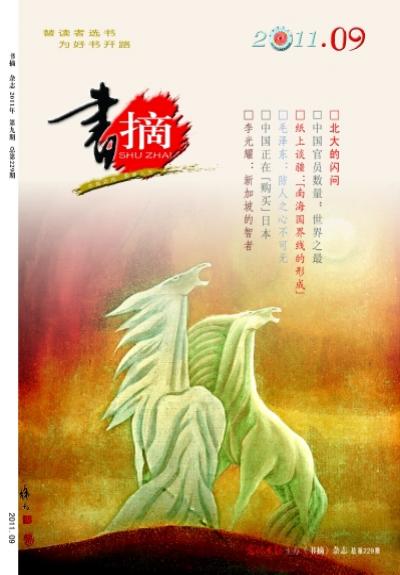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