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下简称《新探》)1997年6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隔年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当时三联书店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告诉我,书店负责人预测,这本书就是面向专业以外读者的,所以印量颇多。十年后的2007年和2008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和与辽宁人民出版社有联盟关系的人民出版社分别再版,加上这次三联书店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繁体版)再版,前后20年,《新探》中文版共出六版。其间还出有日文版(2004年)、英文版(2015年)和韩文版(2018年),新的英文版也在积极筹备中。2009年由中国、韩国和日本出版人组织的“东亚出版人会议”发起编辑东亚地区20世纪中叶以来人文思想文化100种优秀著作的《东亚人文100》,《新探》作为中国香港地区推荐的六种书之一入选。
在这20年间,有《苏秉琦文集》(苏秉琦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苏恺之著,三联书店,2012年),《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赵汀阳、王星选编,中信出版社,2016年)出版,可以与《新探》相互参照。
在这20年间,考古学科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特别是开拓了新领域。先生在《新探》一书中所阐述的学术思想仍经常起着指导作用,具体观点也被反复证明。《新探》一书也为历史学和专业以外如社会学、哲学、文学以及地域文化史等学界的学者所关注。费孝通先生从学科的长远建设评价《新探》的出版。哲学史界在研究“天下”和“中国”概念时特别注意苏先生学术思想中的哲学分析和推想(见《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赵汀阳代序)。金庸先生的作品以开放的观点处理中华多民族关系,正是受苏秉琦先生《新探》一书的启发(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座,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讲座,2007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编、每省一卷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和袁行霈先生撰写的“总绪论”,也大都有对苏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和引用。
《新探》一书有如此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常常使我想起1996年底在深圳写作《新探》时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对此,我曾有过两次集中回忆(《文物天地》1997年5期和《新探》日文版序,日本言丛社,2005年)。这次撰写“新版后记”时,正好读到陈之藩先生《智慧的火花》一文(见陈之藩《蔚蓝的天·旅美小简》,黄山书社,2009年),文中讲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富兰克林中心有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智者的旅店”的建筑制度。这种建筑“是让智者休息、乘凉、聊天的地方。研究所方面并不计较这些‘旅客’的工作,只是供给他们安适的环境。在闲暇的时间,让他们去思想,去做灵魂深处的探险工作。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即是希望在这种环境下,让学者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以映照这个时代”。由此想到当年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总编辑力邀苏先生到南方,将我们安排在深圳贝岭居那处闹中取静的优雅环境,最初也是无任何具体任务,只是想把先生以前发表的文章选编一本文集,而任凭我们自由思考交谈,不也类似于陈之藩先生所描述的那种“智者的旅店”的美妙境界吗?
就是在那个贝岭居,苏先生住进后心神愉悦,思维清晰,谈锋甚健。我曾回忆,在冬日的南国,每天先生由我陪同,或廊屋促膝,或庭院漫步,展开思想的翅膀,尽穿历史隧道。先生不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不少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在有关《新探》写作的回忆文章中两次选用了“捕捉火花”作为标题,一次是收入本书附录的《捕捉火花——记协助苏秉琦先生撰写〈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又见2004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日文版和200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后记);一次是为北京大学120年校庆撰写的回顾苏先生晚年学术思想脉络的文章:《捕捉火花——陪苏先生聊天》(见蒋朗朗主编《精神的魅力·201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后一篇文章还记录了那年深圳谈话内容中未收入《新探》一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人类文明一元性”。为此,趁这次《新探》由三联再版的机会,将后一篇文章中记录这一观点的有关内容加以摘录,作为这篇“后记”的结尾。
“人类文明的一元性”是苏秉琦先生在论述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提出来的,先见于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开馆时举办的“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生的致辞。致辞在谈到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都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之后,说这“证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元性’”(见《苏秉琦文集》三,22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三年后在深圳,先生又几次讲到这个观点。记得那次刚刚到达深圳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先生就谈到,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还是从一元论考虑,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隔天又进一步补充说:“世界文明史一元化,指一个地球,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此后几次谈到这个话题时还举清朝为例,说清初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就与以渔猎为本的满族所培育的“长城内外是一家”的理念有很大关系,还联系到现实如联合国的产生和最高理想等。那次从深圳回京不久,先生在家里接受了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古兆申先生的专访,专访结尾时先生再一次说道:“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这次专访在《新探》出版的次月,刊于《明报月刊》1997年7期,是苏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人类文明一元性”可以视为先生考古一生中最后的学术思考。
对于先生有关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论述,我以前只作过介绍,并无深解。直到近些年,中国考古界与世界合作交往日趋频繁,研究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也渐多起来,我也有机会留意和考察西方一些典型遗存并关注东西方文化关系,尤其是面临现实世界今后走向的疑虑,对先生这一观点才渐有感悟。我一直在思考,从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学科研究,到提出全球人类文明一元性,其间有较大的反差。如何理解先生学术思想的这一跨越?重新阅读和理解《新探》一书的中心思想,答案似乎渐渐清晰起来。以五千年文明起源及其来龙去脉的实证研究与恢复“四裔”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独特地位为重要内容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从时空范围具备了与世界比较和讨论相互关系的条件,而且突显中国在“地球村”中“举世无双”和“中国是大头”的地位。苏先生曾这样记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它所提供的对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作出纵、横发展的“庖丁解牛”式的辩证统一的研究的条件,在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所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大头。
我曾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初创,面对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需要的是学术上的勇气。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则是充满了自信,是来自于对多年来学科健康发展的自信,由此又想到费孝通先生对《新探》一书的评价。费先生提倡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和前提的,他于1998年在为北大百年校庆撰写的《北大百年与文化自觉》纪念文章中特意提到刚故去的苏先生和新出版的《新探》一书,说这本书就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因为这是一本“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的著作,“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费先生与苏先生都力主中华民族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费先生倡导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与苏先生的“人类文明一元性”又不谋而合,两位老人心灵深处的再一次沟通,不正是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将人类未来发展大趋势的预言,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从而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吗?所以,苏先生曾经乐观地对我说: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作者:郭大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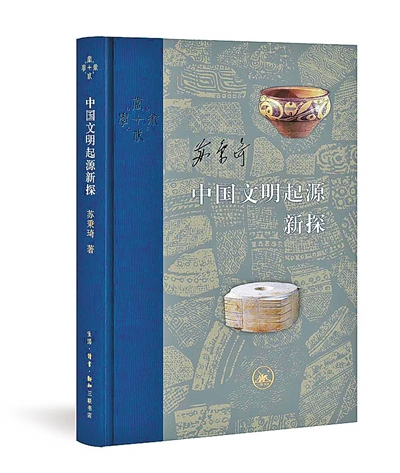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