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一本好书都会具有值得挖掘的多重价值,《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也不例外。该书聚焦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以访谈录的形式再现了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马敏、罗钢、葛剑雄、陶思炎、胡星亮这十位“堪称一代学术精英”的大师兄的艰辛求学历程,勾勒出新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是研究中国近代阅读史、高等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个体如何融入时代的有效指南。开山大师兄们,一向认真回应时代,始终自强不息。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前,他们或者晴耕雨读,或者工读结合,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等来上大学的机会之后,得以顺利实现升学的梦想,师从良师,在专业领域里自由翱翔。70年间,他们很好地处理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成为受人尊敬的开山大师兄。他们光大了中国文科学术,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楷模。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
回望开山大师兄的成长历程时,人们可能会故意夸大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环境对个体的压抑,或者借开山大师兄的教育经历而批评当下过于标准化的教育与学术管理体制。这些想法和做法不无道理,但也值得警惕。诚然,外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十分巨大,但葛剑雄说得好:“一个人的成功首先是个人的天赋,第二是机遇,第三是自己的努力,前面的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左右的,自己的努力是可以选择的。”与其自怨自艾或者感叹生不逢时,不如做好自己,奋发向上。
阅读《开山大师兄》,最令笔者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在别人看起来并不太美妙的时代,在大师兄们的眼里却没有那么糟糕。马敏说:“虽然那个时候知识荒,要找点书看很不容易,但只要用心,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钱乘旦也坦言,“如果说自己抓紧了,能读很多东西”。根据他们的经历,知青们如果愿意学习,一般不会受到恶意阻拦,并不存在“插队的知青在农村爱学习,找时间读书,贫下中农不许他们读,敲锣打鼓去捣乱”的情况,“那时候的农民对读书是非常支持的”,只要干完该干的活,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莫砺锋因为年龄超限无法报名参加高考而发愁时,乡亲们还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以英语特长生的身份报考。最不幸的要数李伯重,身处云南边境,学英语有叛国的嫌疑,他也曾因此受到检举,但最终还是过关,“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油灯下读书”“学习始终没有中断”。
开山大师兄们都是“在精神上挨过饿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渴望读书,“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书”“看书基本上没有停”。交换和借阅是常见方式,“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相互借阅,各个人家多少会留藏一点图书,有的是以前图书馆借出来的还没来得及还”,有的是从被撬开门的图书馆拿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会不约而同地借批《水浒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机会阅读相关书籍。最特别的办法来自葛剑雄和马敏,前者通过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军事文选》学习英文;后者用糖果贿赂有藏书的人家的孩子,鼓动其将家里珍藏的书偷偷拿出来给他看。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不问主题和专业,也不管条件的优与劣。马敏在别人喝酒唱歌的时候,拿棉花塞耳朵里排除干扰专心读书,莫砺锋承认自己的十年插队生涯“不算完全荒废”,利用空余时间“不惜工本地背诵作品”“背过好多东西,《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背过,《古文观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唐宋诗歌能背诵的也有“好几千首”,又将许国璋英语“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体抄了一遍”。尽管这样的阅读零零星星,很不系统,成为开山大师兄之前,他们还是读了不少文学、史学、哲学的书籍,知识方面应该打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这对他们日后的专业发展和特色形成大有裨益。
读书也没有影响他们作为知青应该担负的本职工作。莫砺锋“务农之余就是读杜甫、读苏东坡,读了以后心情比较淡定”,曾经连续两年被评为“扎根农村积极分子”;陶思炎很快被借调、招工,又被推荐上大学;俞可平是植保员,高考时水稻处于生长的关键期,他没有因复习而请假,直接“从田里爬起来去考试”;在工地劳作的马敏也是“照常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复习”;葛剑雄一边抽空读书,一边进入专案组做调查和管理工作,他“有三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在公检法上班”。这些开山大师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要尽可能做好”,做出特色。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
大师兄之大,不在于年龄与资历,而在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与大发展。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学术与人生,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勤奋读书,补差补缺;另一方面,在各自导师的指导下,积极追求多学科整合与融通,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制订明晰的个人规划,是开山大师兄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李伯重、庄孔韶的父亲都相信“总有一天得恢复考试”,暗中指导他们学习,并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提供了影响他们一生的求学建议。其他几位开山大师兄没有这样的条件,却也能本着对求知的渴望以及对自我的责任感,审时度势,相机读书。胡星亮坦言自己“做事太有计划”“八到十年之后做什么,我现在就非常清楚。”葛剑雄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决定不再去念文学,而历史地理不错,就选了历史地理。”罗钢“觉得几乎20世纪所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都可以在中与西、左与右这两个光谱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在博士论文之外写了《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又与人合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起源》,借此讨论“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开山大师兄们有时还要承担行政工作,莫砺锋当过系主任,马敏当过校长。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专业研究,此时,他们的规划意识再次显现。莫砺锋“想了一个主意,论文写不成了,就写随笔。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时间零碎也没关系,就在那一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马敏“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经常工作到深夜”,自忖“细致的史料考证需要大量时间,我做不了,就研究宏观一点的问题,包括写深度书评,写了不少,把自己想做的、比较精致的学术工作往后推。我利用零星时间来积累,退下来了就赶快做”。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个人职业生涯规划需要眼界和格局,开展具体学术研究同样需要眼界和格局。“只有放宽视界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开山大师兄们的共识。上山下乡期间,他们有什么看什么,结果就是读书很杂,知识面非常广,已经有了一定的眼界。进入大学之后,在老师的指点下,大师兄们进一步拓展视野,追求更大的格局。他们既专注于专业,又放眼其他学科;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国外。一面打通学科壁垒,让书斋与田野贯通;一面关注中外文化关系,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尝试用比较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引进西方话语、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方法之时,他们特别注意鉴别真伪,区分异同,考虑其适用性,努力探寻适宜的研究方法,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马敏坦承,“做学问光在国内是不行的,一定要开阔眼界,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要完全用西方理论套中国的东西,而要把中国这一套活生生的东西解释清楚”。莫砺锋重视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同时还特别注意从《唐诗杂论》《谈艺录》《管锥编》《古诗考索》等著作中学习前辈的古典文学研究法。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则希望自己能够“运用一切事实证明有用的研究工具”,养成“多视角观察分析现实政治的习惯”。庄孔韶重视“多学科知识基础”,也重视“问题意识和过程研究”,他指出,“过程研究怎么分配,怎么找学术点,这是一个博士要钻研的……过程研究还需要思考跨越时空的关联性与差异的解释”。陶思炎倡导建立一种“超学科多层次复合研究法”“把实物的、文献的、口头的、图像的、行为的资料都作为考察的领域,同时还要注意知识的拓展性、跨界性和完整性。”钱乘旦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史料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观点,同时还推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在老师的指点或引导之下,开山大师兄既能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合理规划,又能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最终掌握甚至创造了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绩,卓然成家。莫砺锋及其唐宋文学研究被其他学者称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陶思炎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进步,使这个原本落后的学科取得了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的资格,“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李伯重、钱乘旦、俞可平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马敏、罗钢、葛剑雄不仅术业有专攻,而且长期在高校领导岗位上任职,显著提升了各自学校的教学风气、治理水平和办学实力,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
扎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开山大师兄中有很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70年间,他们的遭遇可谓坎坷,时代和命运给予他们的机会并不多。诚如葛剑雄所言,“现在老是有人感叹机会不多”,事实上机会是个人争取的,也是个人创造的。开山大师兄的成功经验提醒我们,人一定要有大视野、大思维和大格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要尽可能做好”。用马敏的话说,就是“当知青就当一个好知青,老老实实修好地球;当工人就当一个好工人,拧紧每颗螺丝钉;上大学就做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学海泛舟;教书就好好教书,把学问绣出花来;当校长就当个称职的校长,在其位而谋其政。一步步走来,人生也就一步步走向成功。”
今天,这些大师兄们依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莫砺锋新近出版了十卷本《莫砺锋全集》,又与妻子联袂出版了随笔与书信合集《嘈嘈切切错杂弹》。他表示“只要还没退休,还会认真地工作,还会好好开课,继续带研究生,有机会就继续做一点普及工作”。陶思炎、李伯重、罗钢等人也纷纷表示,“还是像这样做下去”“能够这样坚持做下去就可以了”。陶思炎相信马克思的话,“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钱乘旦声言,“研究成果要拿到大众那里去检验,要能够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俞可平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学术生命是和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有价值”,主张“以学术的方式和政治实现互动”,希望能够写一些通俗文章,普及政治学知识。罗钢也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学术生命是和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有价值”。葛剑雄则指出,“要把学术研究的结果跟政治的需要结合起来”,要“出于公心”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开山大师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开山大师兄》这本访谈录也值得细读深思。阅读这本书,不啻与开山大师兄直接晤谈,可以深入理解他们的人生态度、追求与实践。苟能会心得意,恐怕不仅胜读十年书,也不止于获得学习方面的教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新时期。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又迎来新时代。在这个“大转型、大变革时代”,我们应该向开山大师兄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行动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时代互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
(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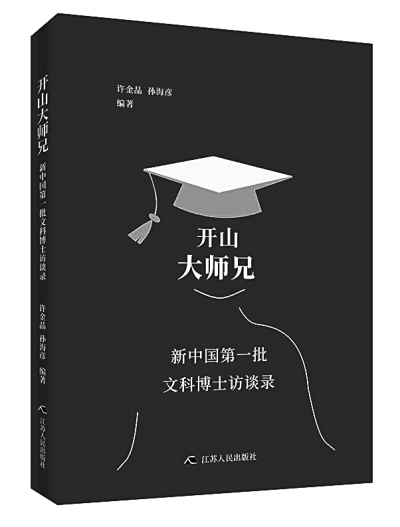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