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故情愫】
回忆故乡的风车
在乡村,它是最好看的东西。
远远看,它像一匹马安静地站立在场院,四周脱粒后的稻草、麦草,是它吃的饲料。现在它吃饱了,正在反刍。
这种幻觉持续出现在我的童年。常常,在清早上学的路上,看见谁家门前场院昨天还堆满麦捆,这会儿却忽然空荡荡的,首先想到是被站着的那架风车吃了——你看它吃饱了那么满足、平静,脸上还有笑。
在秋收后的夜晚,我们常到场院里玩耍,风车就成了我们的玩具,当然它是大了一些,我们只能这里摸摸,那里瞅瞅,有时就敲几下风板,听它嗡嗡的回声;最大的动作,是轻轻摇几下风轮的手柄,制造一缕缕小风。别的大动作不敢乱做,大人说,风车脾气大,坏了不好修,就不出风了。
那时,在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的眼里,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性、有感觉的,山有山精管着,河有河神护着,花里面住着花魂,石头里藏着精灵,何况风车,它长着马的样子,它有眼有鼻有荡气回肠的胸膛,它世世代代帮助着乡亲,都知道它是风车,但在我们眼里和心里,它就是一个庄重的生命,一个爷爷辈分的长者。
最难忘在月夜看到的风车,月光从天上落下来,落到风车上,风车的影子掉在地上,比风车要小,好像是风车生了个孩子,风车似乎也纳闷自己怎么生下个风车孩子,于是就定定地端详着那个小风车。一直到月亮落山,风车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孩子的老风车。
我曾经看过村里的木匠做风车,风车是农具里结构最复杂的一种,能做风车的是手艺最好的木匠。木匠叔叔把木头锯开,裁成长长短短宽宽窄窄厚厚薄薄的木板、木条、木楔,他不停地眯着眼睛用墨线量,用角尺画线,不停地用锯子锯,用斧子削,用刨子刨,用凿子凿,用锛子锛,用锤子钉,用砂纸磨,他有点神秘,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与风有关,他在制造风,他的手里似乎握着风……从他手里,慢慢地就长出了一架漂亮的风车。
看着崭新、光鲜,显得十分天真和欢喜的风车,我就幼稚地想,木匠叔叔做一架风车,这要比妈妈生孩子更不容易。孩子是在妈妈的肚子里自动生长的,这风车可是一点点用手制造出来的,里面的风都是木匠叔叔手把手盘养出来的。我对匠人的尊敬,就是从一架风车开始的。
麦子打了,稻子收了,风车吹走了秕谷和草絮,吐出了所有的粮食,也把最后一股风交给季节,风车闲下来,静静地站在墙角或屋檐下,清净无为的样子,像一个单纯的老人,连多余的心事都没有。
世上有的是各种各样的风,狂风、飓风、台风、龙卷风、冷风、热风、阴风、暴风……乡村的风车,古老的风车,它制造的总是温柔的和风,带着五谷的馨香,飘着草木的清气,曾经,它用它深沉的呼吸,吹拂着大地上的乡亲,吹拂了我童年的衣襟。
闭起眼睛,我又看见,月光里,那干干净净的风车,安安静静的风车。
想念小村
小村很小,一二十户人家,地名听起来也很小。这小小的地名需轻轻地、抿着嘴叫,才能叫出那小小的味道、小小的意境、小小的风情。如果你大张着嘴吼叫,会吓坏了她,会惊了她的魂儿。不信,你试着大声吼一句:孙家湾!看是不是没有了孙家湾的味儿?孙家湾飘着淡淡的野花香味儿。孙家湾像一个新婚的小媳妇,青涩、害羞、爱笑,朦胧中透出刚刚知晓什么秘密后的不好意思,还流露一点隐隐约约的风流。
你肯定不能大声吼叫孙家湾,只能轻轻地、软软地喊她。
李家营、张家寨、汪家梁、富家坝、杨家坪、袁家庄、吴家沟、王家坎……她们都是孙家湾的姊妹。她们都是很小很小的小村。
一只公鸡把早霞衔上家家户户的窗口。
一群公鸡把太阳哄抬到高高的天上。
一只猫捉尽了小村可疑的阴影。
一只狗的尾巴拍打着小村每一条裤腿上的疲倦和灰尘。
一条小路送走远行的背影,接回归来的足音。
一座柳木桥连接起小河两岸的方言和风俗,彼岸不远,抬脚即达。
一头及时下地的黄牛,认识田野的每一苗青草,熟悉小村每一块地的墒情。
一架公道正派的风车,分辨着人心的虚实和小村的收成,吹走了秕谷,留下了真金。不管外面刮什么风,这古老的风车,她怀古,她念旧,她一年四季只刮温柔的春风。
一缕炊烟从屋顶扯着懒腰慢慢升起,与另一缕炊烟牵手,渐渐地与好几缕炊烟牵绕在一起,合成一缕更大的炊烟,淡淡缓缓地,又热热闹闹地,向天上飘去,结伴儿要到天上去走一回亲戚。
一架高高的秋千,把小村的笑声荡向云端荡向天河,只差一点,就把天上想家的织女接回来了,可惜就差那一点。于是小村的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荡了一年又一年。
一棵老皂角树,搓洗着世代的衣裳,小村的布衣青衫,总是那么朴素洁净合身得体,一年四季都飘着皂角的清香。即使走在远方的街头,闻一闻衣香,就能找到你的老乡。
一弯明月是小村的印章,盖在家家户户的窗口上,盖在老老少少的心口上,有时就盖在大槐树上和稻草垛上,盖在孩子们的课本上。
小学放学的学娃子,边踢石子边背诵“两个黄鹂鸣翠柳”,小村的树上就歇满了唐朝的诗句,家家户户就记住了一位姓杜的诗人。
村头那口水井,滋润着小村的性情、口音和眼神:淡淡的、绵绵的、清清的……
小村很小。小村的世面不大,小村心地单纯,心事简单,话题也简单。小村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悲大喜,习惯了平平静静过日子,小村的夜晚没有噩梦。
小村很小。小村的心肠软,人情厚,张家娃感冒了,折几苗李家院子里的柴胡散寒祛风;黄二婶炖鸡汤,采一捧邻居菜园的花椒提味增鲜;老孙家的丝瓜蔓憨乎乎翻过院墙,悄悄给我家送来几个丝瓜;我家的冬瓜藤比初恋的后生还要缠绵多情,绕来绕去非要绕进老孙的地里,于是,几个比枕头还大的冬瓜蹲在那里,傻瓜一样守着,不走了。
小村很小。小村的脾气好,性子慢,庄稼不慌不忙地长着,孩子不慌不忙地玩着,大人不慌不忙地忙着,老人不慌不忙地老着,溪水不慌不忙地哼着祖传的民谣,燕子不慌不忙地背着一部远年的家训。除了急躁的闪电和偶尔发脾气的阵雨,多数时候,小村是慢悠悠的——羊儿是慢悠悠吃草的,夕阳是慢悠悠落山的,山湾的那汪清泉,也是慢悠悠说着地底的见闻的。
小村很小。小村的胸襟并不小。小村的天空很大。天,是小村的哲学老师和伦理学教授,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透彻。小村有句口头禅:老天爷在上,把啥都看着呢。小村早就明白:在天下面,谁都是小小的,神仙是小小的,皇帝是小小的,村长是小小的,人啊鸟啊猫啊狗啊蚂蚁啊都是小小的,谁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小村没有势利眼,小村没有奴性,小村不崇拜什么官啊长啊,小村只尊敬君子,君子是大人,君子是懂得天道人心的人,是有情有义的人。因此,厚道和本分,是小村对人品的最高评价;善良和仁义,是小村的身份证和墓志铭。小村虽小,小村不出产小人,小村最看重良心。
小村的鸟不卑不亢地飞着,小村的狗不卑不亢地叫着,小村的河不卑不亢地流着,小村的云不卑不亢地飘着。
小村夜晚星星很多,密密匝匝像熟透的葡萄。老人逗孩子们说:“那么多葡萄,祖祖辈辈也吃不完一小串。”
“嚓”——几粒流星划过小村头顶。
孩子们说:“天上的孩子也在吃葡萄。”
(作者为诗人、散文家,作品入多种选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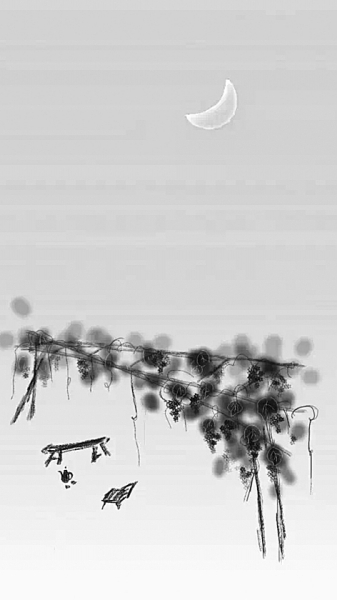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