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和雨落在河面上,升腾起水汽,我的心里也升腾起深深的敬意。眼前这一群治水人,把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看得见的汗水、看不见的心血都熬在了“建污水厂、调试设备、拆除养殖场、保洁监督、生态补水”“强势推进”“雷霆治污”等等这些枯燥又艰难的字眼上,却还能如此举重若轻、谈笑风生。
“沧桑,我真的没什么好采访的,我帮你找人,具体都是他们做的。”
2016年暮春,当我冒雨前往家乡浙江玉环寻找水的故事,一条微信,让我预感到,迎接我的将是一次艰难的采访。
“晨雾绕岛,形状如环,上有流水,洁白如玉。”这是古志《太平寰宇记》中关于玉环的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先辈们就已在这个东海之滨的小岛上种田讨海,繁衍生息,他们兼有山的仁、水的智,纯朴,豪爽,勤劳,幽默,豁达,而最大的特点是,实干,低调。
一个月前,父亲曾经带着我,穿过一大片油菜花地,去我小时候常去的河边看看。他说,记得吗?几年前,你站在又脏又臭的河边,说过一句气话:“老家,我真的爱不起来了。”你每次来去匆匆,都不知道老家这几年已经像你的名字一样,沧海桑田了。
如他所说,水就是玉环的气血。玉环有三水,一是海水。以前,台风来前,老百姓都会惊恐万状,扛着板锄簸箕,敲锣打鼓去加筑海堤。一旦决堤,整个镇就会变成汪洋,还会死人,老百姓叫苦连天。现在好了,漩门港一期二期大坝工程把巨浪牢牢拦在了外面,老百姓再也不愁了。二是淡水。“玉环人民没水喝”这句话几年前很流行,政府“打天落地”想办法,从温州买水,从温岭引水,如今修建了大小诸多水库,建成了海水淡化系统工程,现在自来水哗哗哗的,多少爽。三是污水。前些年的确太脏了,洗菜、洗衣、刷马桶、丢垃圾、排污水,全在一条河里,现在你看看,铲了淤泥,清了垃圾,驳了河崁,种了桃树柳树枫树,电灯亮亮,柳树摇摇,老百姓琴拉拉,舞跳跳,多少舒服,就连水里种的水草,喷泉,也都是有治水功能的。就像一个人,气血和畅了,玉环自然就漂亮了。前几天我坐三轮车,骑车的本地佬还编了好多顺口溜,可惜我学不来哈哈。
父亲的话,让我感动,也为自己那句气话羞愧。因此,一个月后,前往家乡采访治水故事,满心欢喜,不料途中接到采访对象——县政协主席、大麦屿庆澜水系“总河长”老吴发来的微信,像给我当头浇了一瓢冷水。
怎么办?
4月某日15:50,玉环县政府大院。
南方的春天已近尾声,海岛的南风天一起,房间地上就像下过雨,很滑。没有电梯,绕着楼梯往县府大院四楼老吴的办公室走时,脚下要憋着点劲。浙江在全国算富的,台州在浙江算富的,玉环在台州算富的,而我家乡的领导们,居然在这样的楼里办公,忍不住给林县长发了条微信:正在你的衙门里。但忍住了后面那句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寒酸的县府办公楼。
桌上是一盆开着花的君子兰,窗外是绿意浓郁的香樟树,满柜的书籍、墙上一幅幅老吴拍的极富人文气息的摄影作品,使这个简朴的办公室散发出一种清新的华贵气。
老吴是我的师兄,我们的父亲们曾是同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年届花甲,气质儒雅,琴棋书画样样拿手,摄影作品已获得多个全国金奖。我没有当他是领导,他更像是我的一位兄长、文友。
但此刻,我无法说服他,如同他的相机无法摄下窗外香樟树的香气。
“我今年就退休了,河长,我一开始以为是挂挂名,没想到动真格的,治水是好事,就上心了。我就做做监督协调。市里客气,给我评了个先进河长,你千万不要写我,写一线的人,他们更值得你采访宣传。我帮你联系,放心,保证你完成创作任务。”
于是,打电话。
他帮我打时,治水办的人也帮我联系我之前听到的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雇人把自己影响河道的违建房子拆了、全家借住亲戚家的老党员——71岁的清港镇垟心村村民老王。电话打过去后,得到的回复是:“都是应该做的,没什么没什么,不要写我哦。”
还有一个是挪用60多万元“私款”为治水垫付了沙石、水泥、工资、征地款的村支书——清港镇朱家前村村支书老郑。听说要采访,老郑在电话里说:“我只是想着把村里的事情做好,别的也没多想,也说不出什么,我在出差,不要写我哦。”
我呆坐着看老吴打电话,没了心情。我知道玉环人低调,可没想到都这么低调。
终于,老吴如释重负地放下了电话,说:“联系好了,明天我们陪你去大麦屿!”
4月某日18:00,玉环县某餐厅。
一个淡蓝色的塑料药盒子,被老吴悄悄从公文包里取出来,放在餐桌上。他从最左上角的一格里找到一粒药,就着白开水吃了下去。他没有把药盒子放进公文包,而是放在了餐具的左边,用胳膊挡住了。
“你身体不好吗?”
“不太好,好多毛病。”
经他同意,我打开了药盒,一共有七八种药,有治糖尿病、高血压的,有治胃病的,还有一瓶速效救心丸。
当分管治水工作的常务副县长、清华大学高才生老笋风风火火赶到时,第一句话是问老吴:“没忘吃药?”
忘记吃药,是老吴的常态。他吃一餐饭,必须吃三次药,饭前,饭中,饭后。因为身体不好,他停了网球,停了最爱的摄影,但不能停了治水,有时忙得连饭都忘了吃,更何况吃药,但后果会很严重,怎么办?老笋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吃饭时,准备一杯白开水,吃一颗,喝三分之一水,最后一颗药吃完,把水喝光,就知道都吃过了。
自始至终,老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他治水的事,而是让我听有着11年水环境整治经验的老笋聊。老笋两年前从外地调到玉环,跟他的治水功夫不无关系。玉环治水难度特别高,岛太小,工业太发达,源短流急,地质差容易漏,自净能力太差,城市化率又不断提高,人均水资源量基本上不足400立方米,属于重度缺水地区,水生态系统脆弱,如果管道管理不到位,河道就成了污水沟,而经过几年整治,河水清了,所以信心满满,越干越有劲。
在他对“水玉环”梦想眉飞色舞的叙述里,我看到了一个异乡人对第二故乡的款款深情——他说,计划投入1.5亿把整个玉环五大水系全部贯通,用生态补水的方式,把三个西湖那么大的漩门湾玉环湖水补到五大河道里,再经过大循环回到玉环湖,来个大换血。我仿佛看到,古志上“上有流水,洁白如玉”的景象已然重现。
当我好奇他名字里为什么有一个“笋”时,他说,父母没文化,山上干活时常见的笋,成了他的名字。当年,父母为了供他上大学,连一块肉、一根棒冰、一块西瓜都舍不得吃,无以报答,只有好好干。他说,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实干就是王道。
末了他说,我们随便聊,但千万不要写我哦!
4月某日14:30,大麦屿庆澜河畔。
“老吴头犁开做,我们肯定也头犁开做。”
“头犁开做”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像一头牛一样,头使劲往前拱,豁出命干活的意思。一经大麦屿街道陈主任说出来,大家都笑了。
庆澜河畔,春雨霏霏,满目葱茏,两岸的游步道蜿蜒至绿影深处,通透的河面倒映着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民居,很美,很清爽,很宁静。正在巡逻的保洁员说,这条河以前叫“柏油河”,油污亮晃晃的跟大马路一样,现在好了,清得可以游泳了。
陪我们来的宣传部施部长笑着说:“按老文艺青年老吴的话,是可以跟鱼对话了!”
“可是,水质还没那么好,所以,不能搁燥滩嘎。”陈主任又说了句土话,“搁燥滩”是船搁浅在没有水的滩涂上半途而废的意思。
大家又笑。笑声和雨落在河面上,升腾起水汽,我的心里也升腾起深深的敬意。眼前这一群治水人,把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看得见的汗水、看不见的心血都熬在了“建污水厂、调试设备、拆除养殖场、保洁监督、生态补水”、“强势推进”、“雷霆治污”等等这些枯燥又艰难的字眼上,却还能如此举重若轻、谈笑风生。
4月某日16:30,大麦屿街道办事处二楼。
在火山茶袅袅的清香里,我终于见到了一个可以透露姓名的小兄弟。
1975年出生的江新伟,五六岁就在海里赶小海了。他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说话很快。他主管“截污纳管”,每天和老百姓面对面打交道。大麦屿很多地来自围海造田,地基不牢,村民一是担心挖地埋管会影响房子安全,二是有的迷信,说污水不能从家门前过。好在他信访干了八年,又是本地人,还算顺利,但也会遇到“钉子户”。去年十月,岗仔头村居民游某坚决不让施工,工程推进不了,江新伟担心已经开挖的部分会崩塌,而且拖下去,周边居民也会有连锁反应。他多次上门劝说,游某就是不答应。江新伟急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多,江新伟又来到游某家里,游某二话不说把门一锁,走亲戚去了。十月的天已经很冷,还下着雨,江新伟就站在门外等,妻子电话一个接一个催他回去吃饭。当时他也想走,可既然来了,这事就要成!他想,他们找我审批造房子时,心里多急,却要等我们,我找他们,也要耐心等。
“当时,心里那个忐忑啊,跟头上落着乌云一样的,跟涨潮落潮一样的。”
终于,晚上十点多,游某回来了,看到江新伟还在等他,衣服也被雨打湿了,心里过意不去,招呼他进门谈。江新伟用闽南话耐心跟他解释工程对房屋质量不会有影响。他说,你拿个照相机拍下来,如果过几天裂缝有延伸,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游某终于点头。他趁热打铁,马上叫施工队做好周六突击施工的准备。深夜开车回城关的路上,心里说不出的轻松,都听不见肚子已饿得咕咕叫了。
像游某这样算“文”的,江新伟还遇到过“武”的。陈岙路村开工时,两大家族的几十个村民一起围过来,砸铲车,扔工具,推搡,就差动手打了,根本没有商量余地。他想,不能硬碰硬。他在平时积累的村民联络图中,找到了两个大家族的威望人士,甚至找到了北京的乡贤,终于起了作用。当村民肯提条件时,江新伟长长松了口气,这就说明有了一半进展了,真高兴啊。
我问他,父母亲知道你老是白加黑、五加二吗?
他说,嘿嘿不知道。我想,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爸妈在乡下也会高兴的。
去年秋天,我曾踏遍玉环山水,想重新认识故乡、记录乡愁。我闻到了漩门港湿地的水稻飘香,惊艳于坎门东沙渔村的人文品位,我去龙溪山里看海,被万亩盐田震撼,也为鸡山岛的渔舟唱晚迷醉……我一厢情愿地认定故乡是最美的,而刻意忽视它不美好的一面,更不愿向外人道破。而在这场始料未及的艰难采访中,我忽然发现,这些“隐姓埋名”、都说“不要写我”的故乡人,从不避讳它的短处,它的环境,它的水问题,实实在在为它做着事,治着病,圆着梦。我也发现,当我们对触目惊心的官场腐败咬牙切齿却又悲愤无力时,其实,有无数像老吴、老笋、陈主任、小江等等真正当得起“公仆”二字的官员们,正在呕心沥血。
无疑,治水会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欧洲的莱茵河治理就长达数十年,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后续支撑。如今,整个浙江乃至全国,无数治水人的努力换来了辉煌战果,而同时,如何找钱、找人、找方法,如何长治久安,仍任重道远。
此刻,2016年4月的最后一夜,我在灯下翻着新版自然文学三部曲巨著:《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瓦尔登湖》,其中的《瓦尔登湖》我已一读再读。三本书的封底都印着同一句话:“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叶赛宁”。无论国外国内,人家能把环境弄得那么好,我们也一定能把玉环岛变回《太平寰宇记》上描述的仙境!
(苏沧桑,作者曾获冰心散文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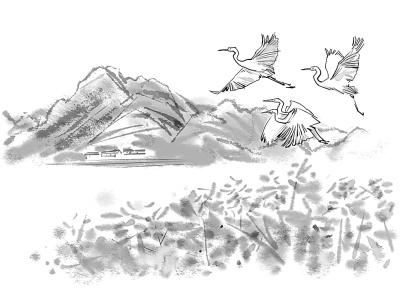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