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影视剧极盛的时代,视觉艺术以其声光色影和感官直觉,从文学作者和读者群中分流了很大的数量。这表明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个人嗜好的选择性的拓展和多样化,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值得警惕的是文学作品日益影视化的负面影响。不少作家在写小说之初,就是以流行的中外电影电视剧为创作的标的,奔着有朝一日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目标而去,期冀获得经济上的高额回报,或者是将已经拍摄完成的影视剧本敷衍成小说,让那些影视剧的追捧者再做一番回味。其对文学造成的最大的伤害有二:一是只顾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营构,而严重地忽略文学语言的戛戛生造,只求浅层次、直观性的表情达意,而忘却了对文学语言的自觉追求;二是只注重那些具有视觉和听觉特征、容易将其转化为画面和声音的场景,而忽略了对人性和生活的更具广阔性的精致描写,作品越来越粗疏简陋,作家的语言贫乏化,作家对人性和心灵的关注日渐阙如,文学的本体性因此越来越弱化,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蕴含着文学的真谛。影视剧以直观形象的艺术手段见长,它可以诉诸人们的视听感官,在短时间内形成很大的观众群,文学则把语言作为自己唯一的工具,同时在更高的层面上,语言的新颖独特,准确传神,以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文学创作,丰富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表达的能力。因而,文学大师,一定也是语言大师。据专家统计,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共使用了两万个词,在古今作家中居于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托尔斯泰,他拥有1.6万个词汇。道理一目了然,作家的词汇量,就像建筑师的材料库,能够娴熟地选择和运用的词汇越多,越能够变化多姿和准确到位地表述出作家想要传达和抒发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出作家对纷纭万状的人性和生活的观察体验的能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蒙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当时在文坛呼声很高的作家,在描写人物吃饭时,写道“吃得满屋喉咙响”,用以形容饥肠辘辘的知青们狼吞虎咽的情形,令人们惊叹其语言之新奇。但是,这样的句子后来在作家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王蒙断言,这位作家的文学创新难以为继。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也曾有一位作家,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连续的三四页中重复出现“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的字样,让人怀疑他在写作时是否真正投入了心血,是否越写越滑溜,写到后边就忘记前面,或者已经词穷。事实上,这两位作家后来都放弃了小说创作。
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优秀作家对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都追求不倦。汉代司马相如的大赋,追求对事物穷形尽相的发现和描述,是一种超级的语言试验,将古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活化在作品中,几乎可以看做是博物志和词类编,虽然对于效果,人们褒贬不一,但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语言空间。而诗歌从四言诗、五言诗到七言诗,从风谣古体到律绝词曲,都是在探索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中完成的。明清以降,小说和戏曲以白话为正体,更是在语言的口语化中寻求内在的精神解放。因此产生一类苦吟冥思的作家。唐代诗人卢延让有一首诗就直名为《苦吟》:“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还有以“推敲”著称的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散文家也不遑多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感叹:“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就文学语言的成就而言,也是空前绝后的,从诗词歌赋曲诔的经典文体,到灯谜楹联乡谣民谚和打油诗,从庄子、老子的名句隽语到《西厢记》《牡丹亭》的精彩唱词,从通俗易懂的《好了歌》,到刘姥姥的“饭前曲”,从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等群芳的诗歌雅集同题竞赛,到薛蟠等浮浪子弟们以悲愁喜乐为题的“女儿词”等,不胜枚举,堪称是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大观园”。
当代作家中,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可以为证;王蒙的语言风格被称赞为天马行空汪洋恣肆,铺陈性和诙谐性很强,贾平凹的古今杂糅文白互动,在雅与俗的两个边界上都达到了极致,刘震云的“弯弯绕”中隐含着作家的“坏笑”和诡异,张炜则以书面语的庄重和诗意沁人心脾。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始,在专家层面上并未受到青睐,它能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播讲而赢得众多的读者,至今都在反复播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遥经常是一边写就一边读给朋友和家人听,是将作品语言的可朗读性和亲近感都化到写作之中,包括“我们的少平”“我们的晓霞”这样的句式,都加强了作品的可传播性,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情感认同。莫言写于21世纪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有很大的变化,其重要的标识,就是对小说语言的声音要素和接近口语化的自觉追求,探索从“可读”到“可听”的新的路径,《檀香刑》将“猫腔”的戏曲唱词融入其中,《生死疲劳》大步后退到章回体话本小说的体式,而《蛙》的私人信件的倾诉方式,也有一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错杂之美。
文学文本不同于影视作品的线性时间和一次性完成,它可以打乱时空顺序,突破直观性的生活场景的局限,而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为揭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提供足够的空间,读者也可以打乱文本顺序而反复地玩味作品。电影专家在讲述不同文本的差异时,爱引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那位老渔民与名叫圣地亚哥的孩子的对话,老渔民口口声声说要拿他的鱼网,说到他做了一锅用鱼烧的米饭,然而孩子知道,“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这种同时在真假两个层面上进行的现实的和心灵的活动,尤其是孩子心中暗暗展开的否定性,很难直接用影视语言表现出来。文学的强项在于,除了听觉和视觉等有形的感官,它可以诉诸嗅觉、味觉,更可以直指人的心灵,它的大量的“潜台词”,远非影视文本所可比。它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与揭示,远远超越了其他的艺术门类。
同时,语言可以表达某些抽象的意念,不受画面和声音的制约。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开篇中所写,比大海更广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这种广阔性,超出了具象的边界,而容纳了大量的玄思妙想和激情涌荡,只有用文学的语言才可以捕捉和勾勒它。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与贾宝玉乍然相见,一拍即合,一问一答中即见出心心相印。宝玉问黛玉,这个妹妹可有玉没有,换了别人,一准会脱口而出否定说“没有”,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一下子摸准了宝玉发问的潜在蕴含,两人话语相激,波澜陡起,别人却不知道个中情由何在,直到宝玉扯下脖子上的玉佩摔在地上,才觉察到此中的浪险渊深。曹雪芹在此,对黛玉进行了深入的心理描写,揭示了宝黛二人确实是天生的知己,而这些心理描写,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在舞台剧,都难以实现小说文本蕴含的完整转换。米兰·昆德拉也曾经说过,当今,在影视和传媒大行其道的时代,小说应该更加自觉地强化其主体意识,让小说所能够发挥其独到的长处,探索人的生存的可能性,在哲学的玄思与人性的探索上花力气开掘深度。他的作品,从早期的《玩笑》,到晚近的《庆祝无意义》,莫不是对人物的精神空间的凝视和深思。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致力于人物的精神层面的解析,探索心灵的无限性,成为20世纪的代表性作品。而我们当下也可以看到,许多后进作家对于人物的精神层面的专注,无论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还是乔叶的《认罪书》,都让我们体会到“心灵拷问”的冷峻严酷,看到文学对人性探索与精神救赎的新收获,也对这些“70后”作家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如果说,情节和故事是小说与影视文本所共有的,那么,心灵的探寻,则是文学得天独厚的禀赋,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缘由。明乎此,坚守文学的底线,追求精神的超越,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吧。
(作者张志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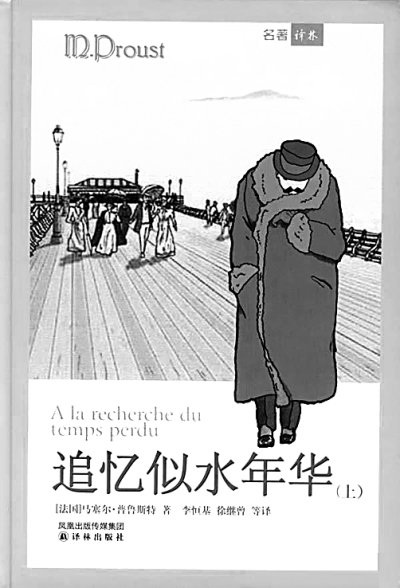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