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机的镜头是什么?这个能够保存影像的机械玩意与摄影师到底是何关系?
我趋向将照相机视为“他者”。摄影师一旦隐身在镜头后面,角色就发生了转化——从一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转化为记录乃至审视社会生活的观察者,尽可能减少打扰和干预,呈现社会生活最真实的样貌。这是我在拍摄记录《百苗图现代图谱》的数年中,努力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十年前,好友曾赠我一套“百苗图研究丛书”,并建议,何妨用摄影记录的方式留存现代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辅之以影视人类学方法,定能做出有别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思索,我们成立了以杨昌儒教授为负责人的课题组,进入实施阶段。
然而,这一课题的展开却异常艰辛。先后6年时间,我与几位主要的参与者一道,跋涉山水,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地拍摄、访谈、记录,仅底片就积存了数万张之巨,调查文本也逾数百万字,随之而来的整理分类,选片定稿,工作量之大,超乎我之前的想象。最终呈现在诸君面前的这一巨册图书,背后所付出的甘苦倒并不是我最在乎的事情,回顾整个课题研究的历程,我更想表达的是若干遗憾。
忠实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是我们在课题启动之初定下的原则。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也是清代《百苗图》的一个延续,或者说是新篇,原因在于,文化因社会的剧烈变革而流动不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按图索骥对应性地拍摄旧版绘录的情景,所谓“现代图谱”,着眼点在当下。但是,由于精力和学养的欠乏,导致我们忠实记录有余,深入研究不足。在编定书稿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后悔,做田野调查时未曾同时采写一部调查日记或者日志,记录下当时的疑问、新鲜的感受,循此线索,追根溯源,探求这些世居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变与不变”,解答文化演进过程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说法是,研究者“要从‘自己’中分化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两方面。‘我’一分为二,观察和思考的‘我’和作为研究对象的‘我’。其实也就是……要从‘由之’进入‘知之’的过程。这个分化就是超脱”。
我以为,好的摄影师应该能融入被拍摄者的生活中去,熟悉并且了解他们,然后再跳将出来,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并记录,从而获得所谓“超脱”的视角。当然这也并非易事,匆匆的旅游者注定只能走马观花、留存此照,好的记录者必须停留下来,生活、观察、思考、等待,最后才是拍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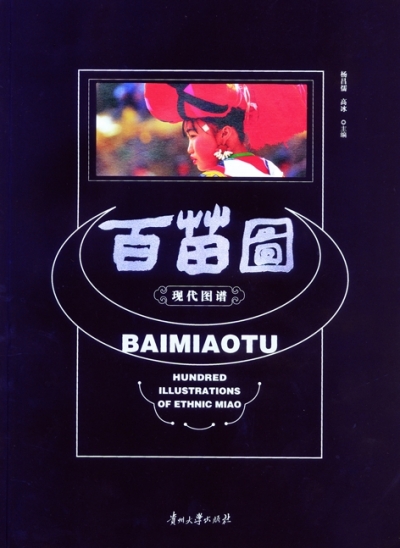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