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套小书,“上海青年文艺评论文丛”,五本,安静地摆在玄关处,是朋友看望骨折的我时落下的,说过了元旦再来取走。我打开那套小书读了起来。无法写作的日子,脑子是空的,触发我阅读兴趣的,仅仅是因为它很快就不属于我。
《肚腹中的旅行者》,作者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写的对象大多和我处于同一圈子,尽管我不喜欢文学以“圈”作为丈量单位。历史、时间、风景、指征,是她文章里频繁出现的词语,她想要在宏大的框架里为当代文学搭建出一个体系。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出文学上的路标,但所有的地图,都是她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我仿佛看见一个弱小女子不断前行的身影,将她检验过的各种各样的作品,一部一部放置整齐,使混沌散乱的文学现场显现出规整的样子来。
《倾盖集》中的“倾盖”出自“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跟这世上的有些人,相识经年,仍如新见;有些人,偶然的相逢,便自倾心,如对故人。“世界上所有的好人可能过去都是一个族里的,具有某种血缘的联系,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失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会凭借这血缘寻找自己的同类。我坚信书是召唤同类的信物,我们把太多时间消耗在觥筹交错中,折射出来的反而是人的曲线,书跟我们的内心却处于一条直线,在阅读面前,我们是诚实的。作者有一种优雅、细腻的气质,因与好书相遇,渐渐浑厚起来,形成了他的趣味:偏爱一种矛盾激荡下复杂世界的呈现。他选定的书是召唤的利器,而他的文章,将利器的光芒擦亮,使他辨别出那些文学的同路人,同时也让同路人辨认出自己。这本集子,无论写西方经典,还是谈论童话,都有一种温文的气息,仿佛在静候知音聆听。
《一星如月看多时》有一股脆劲,谈与文人的交往,一首古诗,或是一部作品。“一星如月看多时”,那些星星不像月亮一样容易辨认,他愿像月亮一样多看一会儿它们。他写作的对象就是那些星星:贾植芳、张中行、张枣、苇岸、王朔……他写贾植芳:“困惑的是,为何我对一个人如此缺乏了解,便写下如此多的感受与臆测?”我想,是因为这颗星星,有一刹那划亮了他的天空,他认真地从各种各样的发光体中,辨认出自己心目中的星星,对它们久久凝视。
在《个人底本》中能看到柏拉图、普鲁斯特、吉本的名字,作者的兴趣不局限于文学,吸引他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这些人经过时间的淘洗还可能留得下的那部分。他善于在人的身上发现特殊性,并从这个人的发展脉络里,展示这个特殊性对人和人生的意义。从这点来看,他更像是我们小说家的思维。他很少去批驳问题,而是将各类书里隐约闪烁的好勾提出来。他用文字表明,那些清澈的人世之光,会从逼仄的缝隙里渗出来,用以照亮人们之前未必看到的景致。
《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开篇就列出一份遇见名单,多是近期在文坛频频引发关注的年轻人,也可以是《遇见一些年轻的作家》,作者是他们的同路人、陪伴者,与他们朝夕相处,希望一同成长。他发现年轻人除了反叛,还有矛盾,他们的书名就显露出来:《残酷虽在,温情犹存》《阴冷背后的温暖》《我们很好,世界很糟》……读着他的文字,这一批年轻人在我心中的面貌越发清晰起来。
这五位作者都聚在上海,彼此充满交集。想到在我生活的城市,搞文学的人都面目不清,偶尔碰见,就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把书从包里拿出来,张望四下无人,塞到对方手里,又继续谈论着股票的行情。我重又翻看扉页,才发现这些人都是批评家。我对这个职业并无感觉,偶尔开会时碰见,各说各话,他们讨论一些我听不懂的题目,而我所抱怨的写作困惑,他们也未必愿意理解,端起酒杯寒暄几句,大家就四下散去。
我像个侦探一样,想进入他们的世界一探究竟。有些人轻易就能找到线索,有些人却神神秘秘,连照片也不见一张,可见他们的性情大不相同。李伟长我见过,他周到、细心,更难得的是有一种对文学的耐心。那个女孩叫项静,原来也写小说,有天真未凿的少女气息,那些持重的评论跟生动的创作,两套思维不知是如何转换的。张定浩给女儿写诗,谈论童话,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气质,仿佛要在这浊世里优雅到老。木叶早就以作家访谈知名了,只是为人低调,一手好文字却不为人知,或许正是这样的善刀而藏,让他的文字里有种切金断玉般的脆劲儿?之中黄德海的信息最少,他仿佛卜居在文字后面的隐士,内心却并不散淡。他的眼睛始终专注地望着远方,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跟他相关。五个人,像五棵样貌各异的树,茂密起来,聚拢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
元旦过后,朋友如约来取走这些书,顺带送我去医院复查。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下楼,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充满了好奇。书放在朋友车的后座上,我不时回头张望,五本书安静地摊开,彩色波点,闪着光辉。
(作者为80后作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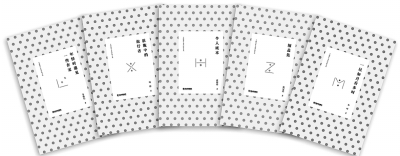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