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下半年先后得到二书,一是中华书局李天飞兄惠寄曹旅宁先生所编《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是缪元朗先生惠寄所编《缪钺先生编年事辑》,书名及装帧均表明这是同一套书,是自然来稿还是出版社有意组织,还有多少种等待面世,尚不得而知。但我深为这套书的编纂与出版而高兴。
缪钺先生、黄永年先生相差逾20岁,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史兼擅、艺文双修。二位先生治学堂庑广大,立身历史学,而皆兼治文学。要研究晚唐的杜牧和唐宋词,不能越过缪先生的《杜牧年谱》和《论词》,缪先生论词所坚守的当行本色观对少女叶嘉莹的影响早已成为学坛佳话。黄永年先生《西游证道书》《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是研究白话小说的扛鼎之作,古籍收藏和版本目录学,则是其文史之外纵横捭阖的另一领域。二位先生又同擅书法,缪先生一手秀美雅洁的小行书,常令得观其书者低徊不置。黄先生书法之外复擅铁笔,徐无闻先生曾对我说,黄永年先生欣赏他的篆刻,特请其治印,徐先生笑说:“我这个永年哪儿比得上你这个永年哦。”徐无闻先生亦名永年,故有此谓。今于曹氏《编年事辑》页162所记,知20世纪70年代方介堪先生为黄先生治鸟虫篆“永年经眼”,因邮寄缺损,黄先生请徐先生重为摹刻;又于页175知徐先生为黄先生抄配所藏明覆宋本《韦苏州集》缺页并作跋语。两位永年先生的交往想必不止这些,但已能部分印证当年徐先生对我说过的话,快何如之。
龚自珍说:“士大夫多瞻仰前辈一日,则胸中长一分丘壑;长一分丘壑,则去一分鄙陋。”予生也晚,但每读定庵先生此语,心中便不免滋生曾得瞻仰前辈风采的庆幸。当年在川大中文系读书,数次聆听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的词学讲座,尚记其用悦耳的普通话洛诵晏小山词句:“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谓以嗡嗡声营造梦境,有助于词意之表达。黄永年先生,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时曾有幸一面。那次他是专门来送关于古籍规划的意见,到办公室时已届中午,傅璇琮先生在中华书局门外小餐馆请饭,黄先生甫一落座便掏出几页纸念起来。菜肴陆续上桌,他还是目不旁视地念着,一桌子人静静地等着他。突然傅先生说,这样吧,我们先吃,黄先生你继续念。黄先生马上停下不念了,大伙儿一起笑了起来。
现在要说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两本书的出版了。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缘于一代有一代之学者。缪钺先生、黄永年先生,无疑是体现当代最高学术成就的一代大学者中的两员。就是这样的一批学者构成了一代学术的中坚,构成了一代学术史的主要内容。就目力所及,从20世纪80年代初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算起就是这么一个传统,即当代学者的“编年事辑”——差不多就是“年谱”了,只是蒋先生谦逊,说“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年谱”“学记”“学述”等,其编著者多是所记述对象的故旧、高徒或嗣孙,比如蒋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高足,曹先生是黄永年先生的门生,缪先生是缪钺先生的哲孙。他们对所记述的对象既有真切的了解,更怀深厚的温情。深厚的温情是其撰著的动力,真切的了解是其著作质量的保障,那么对于今后研究这一时代学术史的人们而言,这类著述的作用之特殊和贡献之巨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教授斋号“崇华”,初次见面,我问这位从本科到博士都就读于清华的“三清团”:“是崇拜清华之意吗?”他回答:“不,我崇拜的是姚华。”姚华先生是清民之交的大学问家和大书画家,时人以刻铜圣手、经纶满腹称之,当年在北京的樱桃斜街举办画展,正在京城访问的泰戈尔亲临展场并发表演讲,其声名之显赫,可见一斑。但姚氏谢世去今不过八十载,生平事迹已经模糊难辨。杨殿珣先生《中国年谱总录》未载其年谱,谢巍先生《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倒有一条,著录内容却只有“稿本,待访,姜亮夫先生见告”一行。杜教授潜心蒐寻始获简谱一种,不过区区二千余字,实在难厌其意,遂发愤亲撰,然积数年之功,亦不过成五六万言而已。当年姚华先生的那些位门生故交,还有前往樱桃斜街亲为捧场的数百位姚迷,假设其中哪怕一两个人有心作“姚华先生编年事辑”,则其必能较后人从事于兹者事半而功倍,那是可以无疑的。
职是之故,我希望有更多的“编年事辑”问世。这类著述之于当代学术史建构的价值不用说了,其中蕴含着的尊崇先贤、发扬师德的古士君子之高致美行,用今天的入时语来说,也绝对是一种满满的正能量,很值得表而出之。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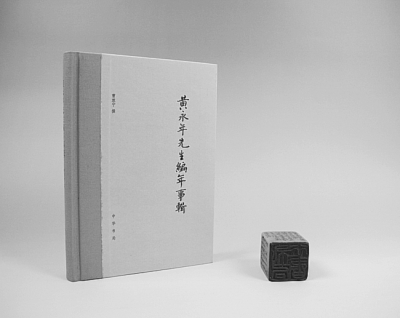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