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秋天,我去西安取贾平凹新长篇《带灯》的手稿,在他工作室的书桌上,看到一本打开着的中华书局版《山海经》,书眉页脚记满文学语言的解释和随机想法。当时平凹对我说:《山海经》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它是中国所有文化的源头,是中国式文化思维的根据;我要写一本新的书,从新解读《山海经》。我以为这是作家要转型的信号,以为他要把坚持了半世的小说暂时放下,开始解读中国古代典籍。因为创作的确是一件异常辛苦的事情,尤其是长篇写作,尤其是对贾平凹这种还在用笔写作并精益求精的人。每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对他都不啻于一场炼狱。所以,如果他真的开始以一种更为轻快并讨巧的方式继续写,从作家的角度,用更为形象和感性的语言进行古籍注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迅速而忙乱,时间被新书出版宣传营销等各种杂事充满,转眼已是第二年的春天。《带灯》的出现,在市场和文坛引起新的震动,贾平凹用别样的唯美的深情的方式,观照着当下中国最敏感的最冷峻的社会现实。这个时候,作家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在工作的间隙,我又问起注解《山海经》的事。贾平凹说,已经开始写新的书了,名字是《老生》。
估计每一个人,包括我,一听到贾平凹又写新书的消息,都会生出各种疑虑:新书是写什么的?到底会怎样?一个作家不停地写,是否可以实现不断地超越?如何才能写出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重复老套了怎么办?……这一次更甚,《带灯》刚刚出版,新书竟然已经写成了!但是从听到作家讲与新书有关的记忆故事,到打开卷本第一页开始阅读,随着时光推回到百年前的秦岭,跟着长生不死的唱师游走两界,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老生》,完成于2013年的1月,与《带灯》的出版时间大致相同。小说是以老生常谈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书中的灵魂人物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他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老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主线,把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连缀成一部大作。《老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中国故事,用中国的方式来记录百年的中国史。
几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话题和关注点已经很少关于《带灯》,而转向了《老生》。在开说这个小说之前,作家向我回忆了特别多的往事,关于他的家乡,他的家人,他的成长,他小时候,和他在各种动荡时代中的独善其身。在回忆的时候,他的烟一直未停,一支续着一支。好像述说的不只是回忆,而是耗神费力的创作。
贾平凹常说,他在写作或思考的时候,最习惯的就是不停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因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抽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
“我的幼年,听得最多的故事,一是关于陕南游击队的,二是关于土改的。到了十三岁,我刚从小学毕业到十五里外去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目睹了什么是革命和革命的文斗武斗。后来,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再后来,我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十几年里高高山上站过,也深深谷底行过。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贾平凹生于1952年,经历无数跌宕和世态炎凉。在《老生》的后记里,他这样讲述过往62年的命运起伏。
所以,《老生》是关于作家家乡的历史,也是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记述历史,用民间的记忆的经历的影像,告诉现世,那个地方有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小说虽然写了近百年的中国,其间的人物事件几乎都是作家听过、见过、经历过的,他是在用记忆、用经验为内心的历史画像。
之所以将新作起名《老生》,贾平凹称,“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则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界,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
书中的灵魂人物老生——唱师,体验了四个故事的时空延伸。在秦岭南部的任何一个村落,几乎每家的丧事都由这个唱师来唱开路歌。不知道是这个职业身份决定了唱师的特质,还是唱师的特质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只有唱师,是超越了时代、制度、人和事,让人体会到人生在世的宏阔。“开路歌是唱阴歌前必须要做的仪式,由我在十字路口燃起一堆火,拜天拜地之后,我就不是我了,我是歌师,我是神职,无尽的力量进入我的身体……我唱的内容一是要天开门地开门儒道佛家都开了门,二是劝孝子给死者选好坟地制好棺木和寿衣,三是请三界诸神及孝家宗祖坐上正堂为死者添风光,四是讲人来世上有生有死很正常莫悲伤,五是歌颂死者创下家业的骄傲和辉煌。”
关于小说中穿插了大段的《山海经》原文,是作家在用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历史,使作品具有很强的空间感。在创作期间,贾平凹曾反复翻看《山海经》,他称这本书中渗透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观念,“如果按照现在人的阅读习惯是读不进去《山海经》的,它句式非常简单,就是几千年前的中国有一个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树,这棵树长得什么样。但是你读进去以后就特别有意思,详细分析每一个字的时候,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文化的源头都在《山海经》,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形成的观念就是从这里面来的。”在写作方法上,贾平凹也借鉴《山海经》的模式,“它是一个山一个山来写,然后构成了它所说的那个世界,我借鉴过来是一个村一个村来写”。
在小说中,《山海经》与主体故事是灵魂相依的关系:《山海经》表面是描绘远古中国的山川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各地山上鸟兽貌异神似,真实意图在描绘记录整个中国,其旨在人;《老生》亦是如此,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写,无论怎样沧海桑田、流转变化,本质都是一样,是写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人的命运。
(本文作者系《老生》一书责任编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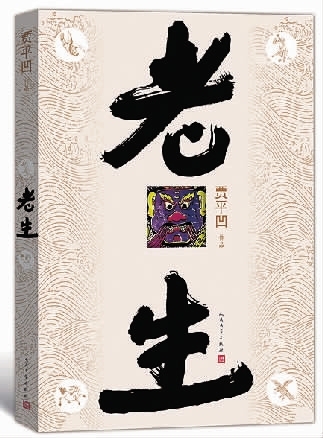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