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诗歌回到了常态,而写诗就是人生积存的语言实现。苏忠钟情于分行文字,或许就是在追求这种语言梦想的实现。他写诗作文,皆出于性情,让那微妙的人生体验、感受和领悟得以释放。苏忠的早期诗作大都观照现实,但从未拘泥于现实,而是带着超越感,将诗歌从世俗的现场推至精神的高度。从专注于商场拼杀,到撤退于幕后的一方宁静,无功利之意,皆性情使然,苏忠不仅仅是在写现实之诗、想象之诗,更是在写人生之诗、命运之诗。
读诗集《醉花僧》(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发现苏忠写诗越来越简洁、轻淡,简到了一种禅意的氛围中,轻到了一种古典的境界里。这可能与诗人的年岁增长、修为加深有关。很多人在面临年龄困境时,退出或放弃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以诗歌“黯淡的前景”观之,好像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可苏忠仍然坚守了下来,从散文到诗歌,他写得越发有韧性,一种生气和力量贯注其中。有人介入时代,有人拥抱先锋,有人走向远方,有人退回内心,都是在面对现实。苏忠的现实可能就是天边一朵云,地上一枝花,心中一菩提。《禅箭录》云:“时间是弓弦/人们只是箭/被命运往后扯/还以为是向前//倒着走的今生今世//有一天 光阴松手/回光返照的一生/来路纷纷苏醒/谁都正中靶心。”这样的诗是需要用心参悟的,否则就可能浮于表层,难觅真义。这种道理,看似诗人间接所得,其实他也是将自我和日常所思置于其中,在发酵和沉淀后,终至成为一种常态、一份信念。
以其性情和气质来看,苏忠不是那种慌乱之中左冲右突的人,他低调、自然。冥想是否是他的常态?这不是什么道德和伦理的担当,它就是生活本身。或许现在所匮乏的,正是一种静下来冥思的习惯。言有尽而意无穷,是我在苏忠的文字中领略的美感。诗是苏忠人生合力的结晶,就像程光炜先生所言,有“空灵”之风,空灵的字里行间透着优雅和从容。
苏忠看似优雅的写作,还是源于他对人生的困惑。当困惑和疑难在现世中无法解决时,诗人以一种持守通向了爱。虽然人生处处有矛盾,时时皆冲突,唯有虔诚地去爱,方可化解悲剧和无常。“有时我相信爱是自由/有时相信爱是宿命/因为魂灵扛不动这一切/所以连肩膀都成了上帝的石头//不负责任的爱 我如此自责/针芒涨成了一把寒刃/我左冲右突从南到北/却发现它一直如影随形悬着//她利剑她天使/说相爱 她是寒刃/说不爱 她是天使/宿命和自由它反复无常”(《无常》)。这人生的无常,皆在这自由与宿命之间徘徊,谁也不敢说自己就真的参透了人生,完全理解了爱。爱是理想,它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和传达的某种情感,只有在具体的爱之实践中,才能获得对其切身的感悟和认知。
苏忠的诗有时就是呈现一种此在的状态,有辩证,有冲突,但更多的则是不可言传的深意和韵致。“许多年以后 我依然没有弄清/我是在鸟鸣中看见了春雨/还是在春雨中听到了鸟鸣”(《雨中》),这看似感觉的错位,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境界呢?时空感在这里通过生命体验得以展开,它是联结某种命运复杂性的纽带。诗人所书写的命运主题都落实在对自然的感悟里,这才是诗意所需要的空间,淡定、悠然,于变化中见巧妙灵动,而又于不变中显出美的永恒。
苏忠的写作是一种人生情感激荡的映射。在众多的自我束缚和戒律禁锢中,诗人有着对自由之境的理解和向往。只有将这些至上的理念诉诸精彩的表达,才可获得其生动和哲思韵味。当那美意顺着心灵的苏醒慢慢恢复,会让诗获得精神和美学上的信任感。苏忠的写作,一向比较节制,但他的文字不时又有着暖意流淌。这是诗人远离喧嚣追求沉潜人生的体现。
(作者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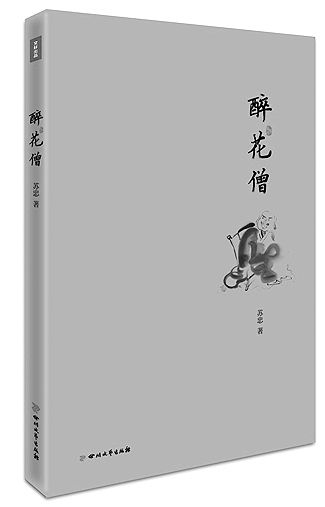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