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市有性别,苏州一定是位女子;如果城市有礼服,苏州一定身着丝绸旗袍。
《锦上姑苏》一书,看书名似乎只是关于苏州丝绸的故事,可细品起来才明白,苏州和丝绸这两个主题都只是作者赞美中国女性的话头而已。读到的、看到的是苏州深厚博大的丝绸文化,而融汇其中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中国经史文章里很难找到的女性主题。
丝绸是中国带给世界的礼物,确切说是中国女性给世界的馈赠。在中国古代,桑蚕丝织从来都是女性的行业。每年春季,皇后都要到先蚕坛祭祀嫘祖,亲自把桑。苏州的盛泽镇是中国著名的丝府绸都,这里的先蚕坛数百年香火不绝。每逢小满之日,盛泽的人们都要酬神三天,因为这是蚕神的生辰。蚕户人家的少女们用体温暖出“蚕宝宝”,丝绸的生命也就从少女的呵护中开始。
采桑,更是极富女性意蕴的工作。相传美丽的秦国女孩罗敷嫁给了秋胡,丈夫远走他乡20余载,罗敷采桑为生,侍奉婆母。秋胡归来,试探妻子,罗敷忠贞不渝,夫妻破镜重圆,这就是京剧名段《桑园会》。战国时,黄河流域还是蚕桑的中心,但隋唐之际,大批蚕户南迁,苏州迅速发展起来。唐朝把天下的州郡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而正是有了丝织业的蓬勃,苏州成为当时江南唯一的雄州。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苏州刺史白居易从来不吝惜自己的才华去赞美苏州的丝绸,“织为云外秋雁行,染做江南春水色。”然而,真正令他动情的,不是丝绸的美丽,而是女性的遭遇。“丝细缫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疼在织女的手上,痛在诗人的心里。《长恨歌》《琵琶行》,无论是贵妃、歌妓还是织女,在白居易笔下,女性如丝般柔美,可总是裂帛一声,玉殒香消。也许正是苏州的丝绸激发了诗人对女性的深刻审美。一千年后,另一位生在江南都会、织造之家的公子更是借着书写女性,把中国文学推上了新高峰。谁能说曹雪芹之所以如此懂女人不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锦绣丛中”呢?
张爱玲曾经写道:“再没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真正懂得丝绸之美的还是女性。用高倍放大镜观察蚕丝,你会发现它不是规则的柱状纤维,而是扁圆不规则的三股纤维交织在一起。一袭丝绸,轻轻摩挲,光滑中似乎带有细细的毛刺,但用身体去感触,又是如皮肤般服帖。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粗糙”,丝绸表面形成多重反射、折射、漫射,造就了它如宝石般耀眼的光泽。这种视觉和触觉的体验,令任何人造纤维都永远无法企及。光华四射的丝绸,激发了女性创造美的更大雄心。刺绣,让丝绸咬破了技术的蚕蛹化为艺术的彩蝶。“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昆曲《牡丹亭》的这段“绕地游”把少女闺怨写到极致:就连最令女孩儿着迷的刺绣也无法摄住少女芳心了。
看罢这本《锦上姑苏》,读者绝对想不到该书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新闻人之手。作者对苏州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本土文化人,这也是为什么苏州人要请他来写苏州的原因吧!作者把女子、丝绸、苏州三个元素交融在一起,笔法娴熟、构思精巧、令人叫绝。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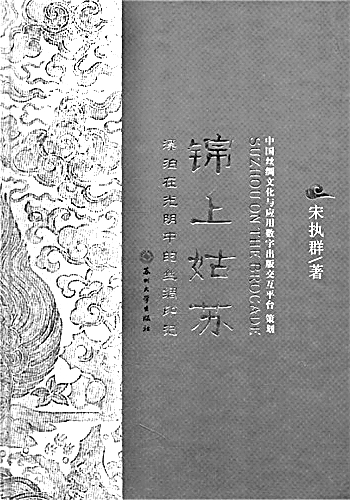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