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满族人,但我对汉字和民乐笛声的痴迷却无以复加。在塞外草原,我度过了一个贫穷、寒冷与温暖交织的童年。按我的家境,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文盲,但老来得子的父亲却让我上了学堂。7岁时,母亲把我送进只有十几个孩子的草屋。快到门口,我抱住母亲干瘦的腿哇哇大哭。这时,我看到,在金秋的阳光中,那个眉目清秀的老师,坐在教室的门槛上,吹响了一支紫红晶亮的短笛。顿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飞起来了……老师吹完了《幽兰》,又吹了《荫中鸟》,然后示意两个好看的学姐,举起一块自制的小黑板,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3个汉字,那是老师给我起的学名。不知不觉,我停止了哭泣……
我打小就是一个没有逻辑概念的孩子,记不住公式,算不好数字,加上贫穷到衣不遮体,又偏偏喜欢好看的女生,自卑从此藏匿我心……小学和中学,作文成为我惟一有信心的方面,成为我继续读书的动力。后来我走出草原,外出求学,世界大了,眼界宽了,我的散文第一次获奖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马年,《人民日报》和《野草》杂志联合举办“金马杯”文学作品征文,我的散文《我会不会忘却姐姐》获得征文二等奖。那时我还年轻,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参加颁奖会,与前辈作家柯灵、叶文玲、徐志耕等先生见面合影,还求了赠言。然而,我之后的文学道路却很曲折:为追求文学的纯粹性而写诗,为实惠省力而写报告文学,还磕磕绊绊地发表了一些小说……直到3年前,出版了长篇叙事散文《回鹿山》,我才意识到,一个天赋不高的作家,不可能是全才,更不能成为写作的杂家。
《回鹿山》的创作,让我第一次把准纪实写作的脉搏。我认为,不论是虚构的“人”还是真实的人,文学离开“人”这个核心,文采再好,意境再佳,也还是缺少感化读者、打动读者的力量。作为一名业余作者,如果让我回答,散文之于我是什么,或可这样说:有作者在场、有灵魂在场的传记和散文写作对于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的最直接方式,是进一步认识世界万物的一双眼睛,是叩问人的灵魂所依的远古笛音,是抒发情怀表达爱意的信物,是一株延续生命乃至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的松下茯苓。坦白说,在文学花园小径往返至中年,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律动、人文情怀和文学修养最与散文相偎相依。
以落魄老兵、贫困乡民的父亲为主人公的《回鹿山》书稿,我曾敬呈给一家有名望的文学杂志。一段日子后,我被通知前往编辑部面谈。那天我特意理了发,刮了胡子,穿上崭新的军装,揣着砰砰狂跳的心前往。两位编辑老师热情接待了我。随后半个多小时,那位编过很多大作的老师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这样带有自传性的散文是没有市场的,换句话说,是没有读者的;作为一个无名作者,琐琐碎碎写这样一个底层家庭、乡民父亲的旧生活,视角狭窄,缺乏高度,这样写作没有前途;如果你写的父亲是一个名人的话……听到这儿,我的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背。躬身致谢后,我像一团棉花飘出编辑部,在楼的拐角处,我停留了很久,以便使快要窒息的心脏恢复过来。
显然,这位老师的评判标准与我的创作初衷南辕北辙。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尽管赫赫有名,但他也说,名人并不一定是英雄,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伟人,甚至不一定是胜利者,之所以写他们,这个或那个人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难,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困难,竭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这个称谓的人。正是罗曼·罗兰推崇的英雄品格,深深影响了我,我最终找到了我要描写的对象——具有英雄品格的最底层最卑微的人,而且是最可让我投入情感的人。我在《回鹿山》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写道:“一想到那么多富豪、政治家和名人被后人树碑立传,我就想到那些地位卑微、生活平常的父亲。偶尔,一个老人的面孔就闪过脑际。我努力回忆,就像早年看过的电影中的某个人物,老人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他就是我的父亲。”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像我父亲这样的普通人数不胜数,他们有着英雄般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永远保持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服强权,也不随波逐流,同时他们都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他人的幸福奉献自身。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然而,曾几何时,很多人却悲观地看到,当作为近代西方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还徘徊在国门之外的时候,金钱反而迅速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某种程度上,高贵、有尊严的“人”竟沦落成“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现实中,变成了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角逐;金钱和财富越积越多,“人”的理想却越来越远……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是事实。既然现实生活如此,文学作品里的“人”一再贬值,也就顺理成章了。其原因是,在这个以金钱为杠杆的社会,一部分作家的理想破灭了,停下来成为瞎子聋子傻子;另一部分作家跑步赶上了金钱的脚步,变成了名利的奴隶……
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智者说,人类不毁灭,文学就不会死亡!坚信这一点,我这个敏感而自卑的人,内心反而渐渐明亮起来——不满和非议越多,说明背后的人群越庞大,在这庞大的人群里,最痛不欲生的那些人,有一天也许会突然安静下来,气定神闲地开始写作,并终将成为少数为人类灵魂写作的作家。写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你有善良的心,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常常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的大脑。
(作者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和散文随笔。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总后军事文学奖和《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长篇散文《回鹿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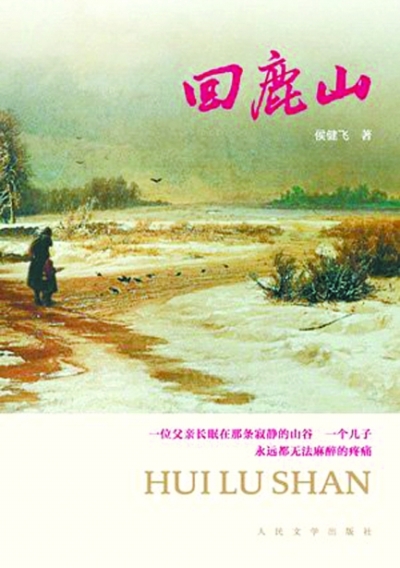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