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蚂蚱
还没学会帮助家里干大活儿,农村孩儿就学会逮蚂蚱。妈妈交给一个她亲手缝的,带松紧性儿的小布袋,由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只要别误了回家。
逮蚂蚱是从草芽出来以后开始的。天气渐暖,枯黄的草色中刚露出一点绿意,就有一种长不大、体型小的蚂蚱出现了。它善于蹦,并且和山坡地一样颜色,如果不盯紧,根本看不着。这种小蚂蚱,刚筑巢的小燕子也喜欢啄它。
到了夏天,蚂蚱数量多了,种类也多了。在长着“车轱辘前儿”(车前草)、屎壳郎滚粪球的土道上,常有一只只带着“忒儿——忒儿——”翅音的蚂蚱飞起。虽然此时多半没有逮它的打算,但也给孩子一丝惊喜。
进入秋天,正是逮蚂蚱旺季,此时蚂蚱最肥。玉米田爱趴“蚂蚱墩儿”,谷秸上爱挂“蹬倒山”,豆秧垄儿和白薯地里爱钻“大蚂蚱尖儿”,矮地阶灌木丛爱有“大驴驹”,还有爱摇头摆须儿的“金钟儿”在草木窠里蹦来蹦去。或大或小或颜色有区别,叫不上名的蚂蚱,还有多种。蚂蚱墩儿短粗,翅短,灰褐色,蹦不起来,最适宜逮。蹬倒山不光体型大,眼睛也大,头上有一对摇摆不定的长须。它目光灵敏,不容易靠近,而且它强健有力的两只后腿上有锯齿,逮它时必须格外小心,先把它两只后腿掐住,否则就会被它腿上尖利的锯齿划破手指。大蚂蚱尖儿和蹬倒山的颜色一致,通身是绿,却身材狭长,超过人的手指,眼睛也是长形的。它善于飞,飞得远,飞起时可见翅羽下红色内衣。逮它时需从它身后捏住翅羽。大驴驹处世孤独,不愿交友,它呆的地方多在谷黍地、矮地阶、场院谷垛上边。它黑色身躯附两片短羽,像腆着肚皮的“暴发户”扣一个不合身的马甲,不招人喜欢。
家长轰赶孩子上坡捉草虫的初衷,是锻炼孩子从小关心家庭,给家庭生活出力。然而,孩子在逮蚂蚱过程中,也学得了知识,寻找到了乐趣。对付各种蚂蚱,他们掌握了捕捉的本事。比如逮善蹦的蚂蚱,就将扬起的小手作金钟罩之状往下扣,在它将要蹦起的刹那间,照准它的头顶扣下去,成功就差不离儿。对善飞的蚂蚱,一定进行死追,一次捉不成,追上几次,它也就飞不远了,最后落入你的掌心。不管是蹬倒山还是其他蚂蚱,门齿都特别发达,其门齿在口腔中占重要比例。这一点,与其习性相关。另外,蚂蚱血是黑的,黑紫黑紫,如熟透的黑桑葚果汁颜色,但闻起来腥臭腥臭。
孩儿们的天性,是你只要把劳动和让他们玩、吃连在一块儿,他们就有充足的动力。大秋时,各种母蚂蚱将要产籽,它们不论体型大小,都揣着一腔籽。有的孩子从家里偷出一盒火柴,就预备烧蚂蚱吃。几个孩子分头行动,拣来细柴枝、干草棍,点燃火,将带籽蚂蚱扔进火堆里,一会儿就能吃到香喷喷、金灿灿的蚂蚱籽了。把揣籽的蹬倒山和大蚂蚱尖儿带回家,此时不像山坡上“野炊”那样急切,而是小心制作,将它搁在煤火炉上边熥,上边压一块“支锅瓦儿”,仔仔细细把蚂蚱盖严。几个小孩儿就在炉台边垂手而立,眼巴巴等候炉火上的动静儿。这时候,小孩们也不像地里那样“嘴头儿急”,吃起来都有点儿风度,慢条斯理,还互相谦让,显出雏形的“哥们儿义气”。蹬倒山的一双后腿,里边的肉像螃蟹腿里边的肉丝一样白细,把它顺向剥开,露出一个肉棒儿,入口香美。当然,他们在地里逮蚂蚱,“疯够了”,余兴还会驱使他们拿倭瓜花当鸟笼子,再逮一两只蝈蝈,装回家去快乐几天。
孩子们逮蚂蚱,最大的受益者是家里饲养的鸡。当孩儿们把鼓囊囊、蠕动着的小布袋带回家,鸡们是快乐的。就由一只彩羽大公鸡领头,带领着芦花鸡、大油鸡妻妾,扇着翅膀迅速跑来,向小主人讨喜欢。此时农家孩儿就像做出了经天纬地的大事业一般,心胸开阔,其乐无比。“男孩儿不吃十年闲饭”,小小年纪就验证了前人的事理。
农村大人也为自家养鸡而行动,只不过他们不是以逮蚂蚱为“主业”,而是在收工之余,顺便而为。他们将逮着的蚂蚱用榆树梢儿、谷莠子穿起来,别在背筐的篾条上,回家喂鸡。农村小孩儿只要他不再使用小布口袋,而学会用谷莠儿、树梢儿穿蚂蚱,就说明他技艺增长,又长大几岁啦。
豆荚摇铃,转瞬就进了深秋。曾经花帐子似的地里庄稼逐渐稀薄了,谷啊黍啊玉米啊等等收割的粮食统统被运送到了场院,场院也就一天比一天丰满。这时,农民的欢声笑语最多。而草虫蚂蚱呢,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熬了。它们把籽产下,留给下一年度生命周期,而自己瘪了肚子,丧失了元气。吮了白露节的露水以后,它们体质更萎,只在午间还稍微有点儿活力。这种状态,老辈农民曾形容过日本鬼子,说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而曾欢天喜地逮蚂蚱的孩子,面对将要死亡的蚂蚱,似乎也失去了兴趣。
逮蚂蚱长大的孩子,从乡亲老爷爷那里也曾听说过蚂蚱的危害。蚂蚱,学名叫“蝗虫”,越大旱之年,它闹得越厉害。它们借助一阵风,由高空飞来,霎时间乌云一般遮盖了村庄的上空,并很快给庄稼带来灾难。一时庄稼地响起像降雨一样的“沙沙沙”啃噬庄稼的声音。农民们悲愤、恐惧啊,又是敲锣敲盆,又是焚香祷告,止不住声地哭泣,却无法阻止残忍的蝗虫集团大军将翠绿的庄稼夷为平地。这般状况,今天中国孩子看不到了,但他们还能从电视纪录片中看到蝗虫在非洲大地上的肆虐,依然让他们产生战栗。
有关蚂蚱,有几种说法。比如:“蚂蚱也是肉”“老虎吃蚂蚱,碎赅(土音读gái)罗”“一根绳儿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蹦不了”等等。但最被人引用的是下边两句,一个叫作“蛐蛐儿也活,蚂蚱也活”,一个叫作“吃个蚂蚱,也分给你一条腿儿”。前一句常为自譬,引喻自己如同草虫活得卑微、压抑,却还有乐观在。后一句讲的完全是情义——连一个蚂蚱都不肯独吞的人,这情义哪里找去?
当年在地里烧蚂蚱吃的孩子,现在都“荣升”为爷爷一辈,还有一部分住进了城市。他们离幼时嬉戏的土地越来越远了。如今的庄稼地,也不同以往,实行了高效农业,又使用农药、化肥,草虫也非常地稀少了。时代大变,当年农家孩儿唾手可得、呈兴奋状喜吃烧蚂蚱之态,情景不再,而此物跃上了细瓷细碗的酒楼餐桌,谓之曰“地方美味”,并且价格不菲。真让当年在野地里吃过烧蚂蚱的上一茬儿人感到滑稽可笑。但是,他还能像当年自己那样被家长轰上山坡,驱使自己孙儿漫山坡疯跑,逮蚂蚱去吗?看来也不可能了。
井拔凉水
一想起了“井拔凉水”,就想起过去温温融融的农家生活和淳朴风情。它所透着的亲,滤着的热,让你永远把它惦记。
北方吃水,靠水井中汲取。有村落,就有水井;有水井,必有人居。从一口苔痕漫布、砌石潮湿的水井处,你可以推断村庄的历史,探知这里先民久远的根基。
北方的水井很多,一个大的村庄,水井不止一口。但最能让你记住并觉得井水好吃的,还是离家门儿不远、自小吃用的那一处。你对那被岁月缠绕而凹陷下去的辘轳头、对那放下水桶时辘轳头转动发出的“呱哒呱哒”的声音,太亲!
这井水真正的神奇处,在于冬暖夏凉。三九天气,打上来一桶水,刚放旁边,不容下一桶的水打上来,先一只桶底儿就已结了冰,桶底和石板台粘在了一起。拔起它时,可见桶底下被压出的圆圆的冰槽儿。然而,水桶里的水漂浮着轻盈的热气。
正格是水温人冻。在寒冷冬季,冒着严寒,头戴放下帽耳子的棉帽,手缩进棉袄袖儿,用棉袄袖隔凉,摇辘轳打水,只有单一受冷的记忆深。真正令你倾心,生发很多快乐和联想,让“井拔凉水”插上翅膀名满人间的,是炎热的夏季。
夏天,井台上充满了欢乐和生机。中午前后,更热闹十分,一把辘轳没有停歇的时候。在家做饭的妇女、放了学帮助家里干活儿的孩子、走起路来慢慢腾腾的老翁,都要去井台打水。水桶虽然排队,人情却在,凡有人说“家里有事”需要插个档儿,谁也不会介意,让他(她)先来。
新打上来的井水,凉气扑面。解暑热,败心火,降暑气。吃面条过水,哪怕就是白薯干儿面“轧捏饹”,浇咸菜汤儿,饭食也开胃。缕缕行行中午下工的人,无不先奔井台,“咕咚咕咚”喝上一气,解了头乏,再拍着肚皮回家去。倘于半路遇见挑水人,决不放过,截住他,手扳水桶张口就喝。挑水者扁担不离肩膀,由着人喝,他站一旁嘻嘻乐。即使喝得只剩下半桶,也决不嗔怨,更不去想入口卫生的问题——都是干了辛苦活儿的一街老乡亲啊。
夜深人静的夏夜,倘未安眠,你照常会听到挑水者“噔噔噔”的脚步响,听到“呱呱呱”放辘轳的声音。那声音流荡于老街,能传出一里多地。
旧时村庄,人们延续古风、厚道,感情不掺假。对老乡亲,一个比一个心肠热,对待外乡人也从不差心。就有一个外乡人到了村庄,又饥又渴,见一个妇女正在井台给牲口饮水,顾不得礼貌,蹲下身就要喝。这妇女见状,急中生智,抓一把“麦鱼子”扔进了桶。外乡人喝水不成,十分恼悻。妇女慢慢解释:夏天井水忒凉,远路而来一肚子心火,急着性儿喝非把肺炸坏了不可!扔进麦鱼儿就是不让你急着喝。外乡人听懂了连忙道谢。这一村忠义待人的好名声也就此传扬出去。
这是一个故事,但和“井拔凉水”有关的风情,也不好不坏地声张在田间地垄里。
夏天庄稼地里干活儿最苦最累。生产队时期每临夏季,都派妇女或弱劳力给干活的送水。水从村里的井打来,干活的在多远,送水的就去多远,或许有二三里地。大热天儿,田里人最盼望的,就是在“歇盼儿”时候有人来送水。远道儿送一次水不容易,怕水“逛激”,送水的往往在水桶上压几片蓖麻叶或放一个柳条圈儿,保持水不外溅。地头歇着的人,耳朵特别灵敏,只要听见扁担环儿击打筲梁的声音,就会有人高兴地大嚷:“大凉来了!大凉来了!”兴奋地跳起。即使上了年岁、最能沉得住气的人,此时至少也挪一挪屁股窝儿。性儿急的,健步如飞,前去接应——甭管是谁把水挑回来,都不容水筲撂地放平稳,抢着喝。轮到最后,剩了小半桶,就有人把水桶举过头顶,桶口朝下,直筒筒地往嘴里灌。喝罢,一抹湿嘴唇,连嚷:“痛快!解气!”凉森森的“井拔凉水”,虽不解饥,却甜透了心。
解决了口渴,自然是头等事情,但田里人不满足,地头上有插曲。他们希望送水来的人是个姑娘,愿意看见一个大姑娘挑着扁担,拧着细腰,袅袅婷婷的身姿;愿意瞻望挑水姑娘走起路来那溜过屁股蛋、一甩一甩的大辫子。洇透了小花褂的汗息味儿,闻着都觉得香!还有个情形,最添乐子:那送水来的是一个爱说爱闹、泼辣开通的胖嫂。她的到来,给田间之人注射了兴奋剂。俗话说,乡亲辈儿瞎胡论儿;又说“荤叔公、素大伯(音读bǎi)、小叔子爱摸哪儿就摸哪儿”,言论特别给人壮胆儿。起先地里男人都还守规矩,顾不得闹,而一旦灌成了水饱儿,就有三五个人现了原形,跟送水女人嚣张起来。胖嫂自不是善茬儿,一边两手拨拉,一边佯作嗔怒,大声叫喊:“小王八羔子,又想找老娘吃奶来了?”大家跟着哄笑,连叼着烟袋杆儿的老人也止不住“嘿嘿嘿”地乐。
“井拔凉水”太好了啊,它亚赛琼浆玉液,十全大补,慰藉人们的心田。
多少年过去了,谁都说“井拔凉水”好喝,从没听说有谁喝了“闹肚子”。那是过去那一代人的福气!出门在外的人,让他记得住的,常常是家乡里的一棵树,和汪在心里的那一口井的水。甭管他在外当了多大的官儿,名气有多高,他都会认为是喝了家乡的井水,长的出息!游子归来,想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拿起扁担、拎起水桶,给家里挑水。并且谁也劝阻不住,由他一趟趟地去,直到给家里老人的水缸,挑得漫溢,湿了一地……
如今不同了呀!甭说现在农村不再挑水吃,用上了自来水,原有水井填的填、废的废,即或真的还有人过街挑水,又有谁去拦下挑水人,当着他的面敢手扒筲沿儿喝上一气?那样做,且不说自己放不下面子,那挑水的也不管他认识没认识到讲卫生,但结果是让人寒栗的:不是跟你翻脸,就是跟你要钱。
“井拔凉水”和井拔凉水带来的风情,从村庄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真是太快。世道轮回,不好多说什么,但那一份人情、风情也跟着没有了,真是觉得可惜。
董华 曾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已出版《还是乡情》《乡里乡亲(上下)》《大事小情》《垄间击缶》《锦灯笼》等多部作品集,并有大量散文作品散见于各报刊。现居北京房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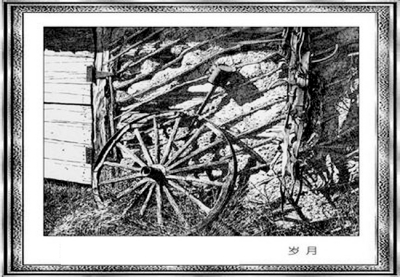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