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央视的一档《百家讲坛》节目,让原本潜心书斋研习清史的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十年来,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并未改变他的学者本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开始研究和写作,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阎崇年为自己的书房起名为“四合书屋”。他说,一个人做成事情,需要“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今年5月,25卷本《阎崇年集》问世,文集800多万字,收录图片2000余张。其中于学术有“一史”即《清朝开国史》,“二传”即《努尔哈赤传》和《袁崇焕传》,“五集”即《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五本论文集;于大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中国古都北京》等。
“在当代清史专家中能够凭一己之力一次出版25卷的,阎老师是第一人。”出版方表示。
五十载心血汇于一书
在《阎崇年集》中,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是阎崇年最新完成的学术专著,凝聚了他五十年从事历史研究的心血,亦是至今国内外清朝开国史研究著作中字数最多的一部。
清朝开国史的时间范围,在清史学界,主要有三种分法:第一种,清朝开国史百年说,即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接受明延平郡王郑克塽归顺、统一台湾,整一百年。第二种,清朝开国史六十年说,即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清都北京,约六十年。第三种,清朝开国史二十八年说,从后金天命元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到清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德帝死、顺治帝立,共二十八年。《清朝开国史》的时间断限,取清朝开国史六十年说。
研究清史,开拓与研究满学,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是阎崇年这五十年间着力从事的三件工作。《清朝开国史》正是将他在这三个方面的文字成果加以汇集,选取研究清朝开国史部分,加以梳理和重新整合后而成。
清史史料之多,如汗牛充栋,任何一位学者想要在有生之年将之阅读穷尽都不可能。“不穷尽研究问题的材料,就不敢说话。但是我当初选了清朝开国这段历史,主要材料基本可以穷尽。还是王国维先生说的那句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读完史料,心里有数了,就可以写。”
1963年到1983年,阎崇年用了二十年时间,阅读完清朝开国阶段相关的基本文献,之后撰写了奠定他在清史界学术地位的《努尔哈赤传》,以及相关论著、论文,再加上这部集大成之《清朝开国史》,在清朝开国史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总数达三百多万字。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应是研究清太祖朝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研究清朝开国的历史,对研究边疆、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很大的意义。今天我们的发展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借鉴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荣,分则辱;合则治,分则乱。”阎崇年说。
关于《清朝开国史》,阎崇年如此评价:“这是我五十年学习与研究、撰著与讲述历史文化的阶段性节点,也是今后学术历程的新起点。”
“北大的邓广铭先生曾经说过,一本书用十年写出来,再花十年修订,要能修订五次,这本书就可以比较完善。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好。《努尔哈赤传》出版三十年来,我就是每十年修订一次。再过十年,到我九十岁时,如果身体没有太大问题,我计划再重新把《努尔哈赤传》修订一次,把《清朝开国史》修订一次。因为十年的时间会让人有一些感悟的提炼、经验的总结和问题的分析,还可能出现新的史料,肯定会产生新的看法。”阎崇年说,“我一直把学术研究看作一个旅程,没有终结。”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史研究名家冯尔康,和阎崇年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样评价他的好友,“阎崇年具有敬畏历史的意识,加上敬业精神,乃渐入治学上的新境地。”
走向大众的“三得一失”
在阎崇年看来,“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2004年起,阎崇年四上央视《百家讲坛》,讲述《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四个系列,共一百八十八讲(集),讲稿分别成书出版。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
阎崇年治史至今已逾五十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为清史学界的诸多同仁知晓,是清朝开国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百家讲坛》的成功,于阎崇年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他几十年厚积薄发将学术成果进行精心转化的结果。冯尔康说,“阎崇年善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予以精准概括与提炼,让人一听就能心领神会。”
近十年来,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知晓,阎崇年自谓有“三得一失”。
第一“得”,传承历史的能量增大。“历史学者就是传承历史,不是创造历史。1994年,我出版了一部《袁崇焕研究论集》,只印了200本,到2004年,10年的时间还没卖完,到2014年也还没卖完。这怎么传承?只能是自我欣赏。而2004年之后,随着在大众中知名度的增大,我写的《袁崇焕传》,一开机印数就是5万,传承历史的能量自然就随之增大了。”
第二“得”,个人见解提升。“我原来多数时间是在书斋里看文献,现在到各地交流和实际考察的机会多了,个人见解也得到了一定提升。比如,关于萨尔浒大战的研究,我过去完全靠看文献;这几年,我有机会陆续将大战的四路行军路线走了一遍,把实地考察的材料都写到书里了。这对前人研究是个丰富。史学研究讲‘才、学、识’,看得多了,识就广了。”
第三“得”,了解了群众对历史的看法。“过去我多是和学界同行交流,不了解普通群众对历史的态度。这几年我接触了很多普通读者,其中一些人的“大汉族”想法非常强烈,让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在研究和宣传相关历史和民族政策的时候,就深感担子更重了。”
社会知名度的不断增加,为阎崇年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条件,使他有机会接触了很多新的史料,在史学方法方面也有了新的拓展,大大促进了他的学术研究。
北京的王府都在二环以内,这曾是清史界和北京史界的共识。前几年,有人在昌平郑各庄发现一座王府遗址,有城墙、城砖、护城河,学界都认为不可能,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阎崇年考察过之后认为,已有的汉文文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从满文文献里找答案。“北京的满文文献我基本都有所了解,没有头绪,只有台湾的没看。恰巧当时台湾学界邀请我去讲学,有机会去查了满文档案,竟然真的找到了线索。其中城墙多厚多高,护城河多长多深,房子的间数,甬道用砖等相关记载都有。台湾方面把档案影印给我,回北京后我又按着这个线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找到满文档案,二者完全吻合,问题就解决了。结论是康熙的行宫和废太子允礽之子理亲王的王府,康熙六十年完工,康熙住了三次。”阎崇年为此写了三篇论文,并分别在台湾和北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得到学界肯定。一桩学术疑案就此水落石出。
一“失”则是由于社会活动增多,阅读文献的时间相应少了。对此,阎崇年深感遗憾,抓紧各种时间加以弥补。
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向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阎崇年一方面感觉快乐,一方面认为责任更大,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我也挨过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红肿。后来我心中逐渐凝聚起一把无形的戒尺:自诫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学术成果要经过三道关的检验,即现时的、历史的、国际的。学术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学术地位不是靠什么头衔和光环决定的,而是靠时代、历史和国际之检验并公认其学术成果而确定的。学术研究既要格物求真,不求官、不求权、不求名、不求钱;又要格物求实,不浮躁、不浮夸、不浮浅、不浮华。学者要有学术理想、学术精神、学术苦旅和学术成果,应严肃学术规范和文人操守,净化学术空气。”
“星云大师说,他的愿望是做一个好和尚。我的愿望则是在下一个十年里,继续伏枥做一个好一点的历史学者。”八十高龄的阎崇年,对未来仍充满期待。(本报记者 吴 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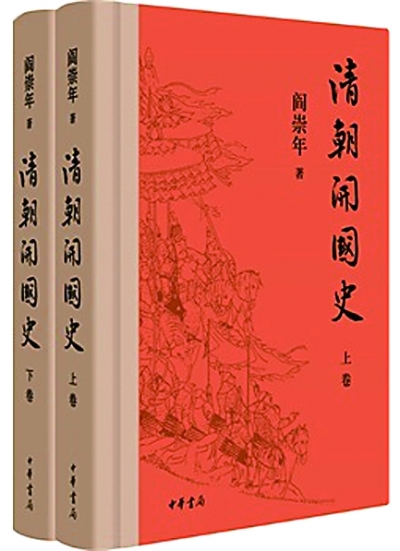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