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医行为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执法者应该看到其显性和隐性后果,现实和潜在后果,直接和间接后果。对造成人身伤害的要严厉打击,没有造成伤害的也不能宽容。
近年来,全国各地以暴力侵害医生的案例不断出现。2013年7月3日,深圳市急救中心医生谢某出诊后,因与患者朋友王某在抢救病患问题上发生纠纷,被王某打了耳光,后被证实为左耳骨膜穿孔。事后当事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由王某一次性赔偿谢某各项费用6万元。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类案件是否仅由当事人和解就可以了结了?
2014年3月26日,深圳市南山医院医生吴某,要求患者在病历本上填写身份信息,遭到患者谩骂,并连续两次被患者推打头部,但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在医院打伤或打死医生,按照现有法律自有处理办法。如果仅造成医生极其轻微的人身伤害,或仅推了医生一下,并未造成明显伤害后果,这应该如何处理?公权力是否应该介入这类案件?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医患关系有问题,但绝不允许暴力侵害。如果允许、宽容这种行为发生,最终受损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通人民群众处于医患纠纷局外,他们的利益会最终受损吗?果真如此,那这类案件就不是普通民事案件,也极有必要对袭医辱医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笔者认为,应该动态地看待暴力侵害医生的事件。这类事件在多次发生后,医生、医院和医学专业学生必然会作出反应,以尽可能保护自己的安全。这种反应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可能是近期的,也可能是远期的。
显性后果:优秀人才被推出这个行业
显性后果比较容易被社会所观察到。如暴力侵害医生的事件多次发生后,一些医院对医生在诊室座位进行了调整:从以前的背对着门到现在的迎门而坐。其目的在于对正在进入诊室的患者的致害可能进行预判,在需要的情形下,可以尽快作出防御性反应。一些医生开始在诊室中放置合法的防御器具,以在受侵害时作出防卫。这种反应倒过来又说明,目前医生在心理上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很不平静。治病是一种对医生的心理状态有很高要求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极不平静的心理状态下,医生的这种研究活动就不可能做好,病人也不可能得到最佳医疗服务。暴力袭医的行为如果不能得到抑制,以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笔者走进诊室时,首先会告诉医生,我是大学教授,您安心地为我看病,我绝对不会打你。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一个改变。另一方面,面对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暴力袭医行为,一些优秀青年及其家长放弃了想进入医疗行业的念头。很显然,医疗服务需要精英,只有让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才对大家的健康有利。但暴力袭医多次发生,把优秀人才推出了这个行业。从长远看,这必然表现为医生的平庸化,这显然对全民族的健康不利。
另外一个显性后果也可以被观察到。现在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开始对病人进行选择,尽可能拒绝具有攻击性的、高风险的病人。理论上,如同出租车不能拒载一样,医生和医院在一般情形下也不能拒绝病人。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些病人被医院拒绝,法律能不能起作用?医院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比如没有床位了。如果有患者较真,想方设法获得真实床位的数据而导致这种借口不好用,那还有其他的理由,如这位医生这两天状态不太好。在这个理由之下,法律还能强迫医生对某个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吗?所以,法律对拒绝的进一步反应,只会导致情形趋于复杂。
隐性后果:提供更差而合法的服务
以上都是显性后果,一些不易或不能被民众观察到的隐性后果也可能存在,而往往更有害。袭医事件反复发生后,由于在这个行业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医生有可能对患者提供更差的服务,而这种更差的服务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合法的,且不易被患者和社会所观察到,或者说很难衡量。
医疗服务与其他服务或商品买卖的根本差异在于,医疗服务的质量很难被准确测定,这就是社会对医生的伦理道德提出很高要求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在医疗活动中,单纯依靠法律的规制,不可能产生最佳的医疗服务。由于医疗服务质量不能准确测定的这一特性,除了法律约束外,必然还需要医生的道德去保证医疗的质量。所以,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如果社会对袭医行为予以宽容,必然导致一些医生对这个行业失去信心,对病人产生负面看法,他们可能不再把医疗活动当作一种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在医疗活动中,医生可以选择对自己最小风险的医疗方案,但这不一定是病人所需要的最佳医疗服务,这种选择完全是合法的。熟悉医疗活动的人都知道,医生最小风险的选择与病人最佳服务的需求,在很多情形下存在巨大差异。
笔者曾经历过一个真实案例。某人的耳膜意外出现了小孔,医生试图用工具取出耳膜附近的血块,当病人表现出疼痛时,医生担心造成进一步损害而承担责任就停止了这种尝试;病人要求恢复其耳膜功能,医生说需要手术,先把耳朵后面切开,再把耳膜补起来。这种手术不仅痛苦,花费也不少。后来这位病人碰到另一位熟悉的医生。医生看后,认为做另一种小手术可能还能补救。于是,这位医生将鸡蛋里的膜放置于耳膜上,最后病人的耳膜功能居然恢复了,几块钱就解决了问题。如果一位医生对这个行业没有信心,对病人也没有信心,会用几块钱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吗?
又如,阑尾炎术后早期需要下床活动,这可以减少肠粘连发生率,减少女性输卵管这一处于阑尾附近器官发炎的概率。这需要医院履行告知义务。但如果医生仅仅告知患者术后每天要下床活动,而不告知其不适度运动的后果,这也符合告知的一般要求,也算履行了告知义务。如果病人给医生留下很多负面印象,医生会怎样把这一信息告知病人?实践中可能还有一些更隐蔽性的情形,比如医生做手术时,他可以把伤口切小一点,切浅一点,也可以把伤口切大一点,切深一点。这种情形病人能知道吗?事实上,医疗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行业没有信心的医生在工作中伤害人的能力比某个手里拿刀的人的伤害能力要强得多,伤害时机也要多得多。而这种伤害,法律很难作出反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法律不可能覆盖医疗活动的全过程,这不仅要求社会不能伤害医生,而且要求对医生有更多的尊重,以换取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不可缺席:公权力必须介入
为避免更严重的情形发生,对袭医辱医的行为不能宽容,必须严厉打击。有观点说,目前的医患纠纷很大程度上是由医疗体制造成的,如药价是政府定的;医生看病是一种高级的科研活动,其价值仅仅通过极低的挂号费来体现,明显不合理,等等。如果医疗体制改变了,现实中不好的医生就会越来越少。事实上,每个行业都有不好的人,问题是不能通过打人来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对袭医行为要严厉打击,对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辱医行为,也不能宽容。假如现有法律对这种行为的严厉处罚有障碍,那可以考虑修改法律。
袭医、辱医行为的严重后果显示了这是一种具有极强负外部性的行为,这种案件已经不是普通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可以和解,但这对消除影响远远不够,因此公权力的介入是必需的,这类案件也不宜以调解方式结案。一般而言,一种行为的负外部性越强,公权力就越有必要介入。以盗窃为例,为何法律禁止盗窃者与被盗者之间私了?其原因主要在于:盗窃行为产生了较多的私人成本和巨大的社会成本。如小区中某家被盗,会直接导致小区中较多家庭在防盗方面的大额投资,这种防御性支出在量上往往很大。私了虽然使直接受害者得到补偿,但不能消除其他居民的恐慌及因恐慌而带来的防盗投资。公权力的功能正是要消除这种负外部性。
在前述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案件中,面对记者采访,打人者王某说:“因一时冲动,打了医生一耳光,现在非常后悔,我向医生道歉。”我们看到,该事件以和解方式结案,打人者也希望事情尽早结束。问题在于,这一行为对医生和医院的影响会随着当事双方的和解而消除吗?众多医生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是否也能随之消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就决定了这类案件的公共性、社会性,以及公权机构在任何情形下介入的必要性。
对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医、辱医行为,我们至少可以依据治安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予以惩处,不能仅依据处理普通民事案件的思路机械地适用法律。对这类新出现的情形,执法者要高瞻远瞩,全面地看到这种行为的显性和隐性后果,现实和潜在后果,以及直接和间接后果。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较多的执法部门一直存在一种不当的倾向:重视显性后果,轻视隐性后果;重视近期后果,轻视远期后果;重视直接后果,轻视间接后果。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公权力的缺位和对违法行为的过度宽容。这是急待改变的。
(作者为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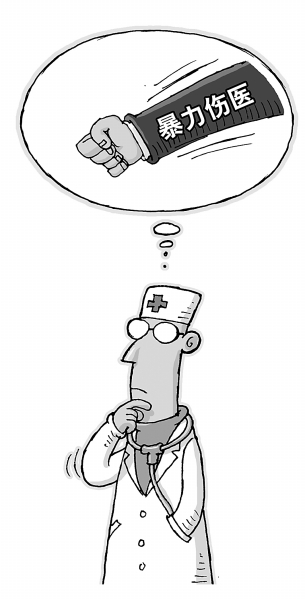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