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爱情是什么样?或许是张瑜和郭凯敏在《庐山恋》中惊世骇俗的一吻,或许是朱时茂和丛珊在《牧马人》中故土难离的坚贞不渝,或许是刘晓庆和姜文在《芙蓉镇》里结伴扫街的不离不弃……那个年代的爱情可能有很多种外在的表现形式,但它们都拥有共同的坚硬内核,那就是一种灵魂超越于肉体之上的,具有普遍的牺牲精神的情感。正如敬文东在《1980年代的爱情》一书的序中所说:“在1980年代,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
在如今这个得到与失去都轻描淡写的年代,我们大概已经无法理解那个爱得隐忍和无私的年代了。那时的人们,并不抱着一定要和对方在一起,有一个完满结局的信念去爱。在他们看来,爱情是美好的,但是为了对方过得更好,他们可以做出最惨烈的牺牲。比如《人生》里的巧珍努力地接近高加林的内心,当高加林选择城里姑娘时,她顺从地接受了,还叮嘱他自己生活要小心,任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平凡的世界》里少安拒绝了润叶的爱情,少平拒绝了金秀的爱情,他们是不爱吗?他们只是不能去爱。而野夫笔下的丽雯,也将成为这些不朽形象中的一员,她们,都是懂得成全的人。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后记中谈起创作初衷时说:“世界上多数人的爱情,都是为了‘抓住’。抓住便是抵达,是爱情的喜宴;仿佛完成神赐的宿命,可以收获今生的美丽。我在这里讲了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这是一个近乎残酷的安排,乃因这样的爱不为抵达,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这样的成全如落红春泥,一枝一叶都是人间的怜悯。”
曾经,书中的他是右派子女,她是造反派子女;文革后,他的家庭恢复了名誉,她的父亲却成为“三种人”;高考时,他考入大学,她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毕业后,他是被派下乡的宣传干事,她是顶替母亲进入供销社的售货员……他们的命运始终在错位中行走,在坚冰逐渐消融的80年代,他们似乎有了更多的自由,然而除了身份上的隔阂之外,他们依然不能毫无顾忌地享受爱情。她认为他是应该飞出山寨的雄鹰,在这条路上,她不是他的同路人,她不愿成为他的羁绊。她是爱他的,她帮他浆洗缝补,为他编织毛衣,鼓励他考取研究生,帮他从颓废中振作起来。然而她一次次地拒绝他的表白,把他推离自己的身边。她在送姐妹哭嫁的时候,对着他唱过这样几句山歌:“高山砍树劈成柴,石头烧出石灰来。将妹真心点着火,烧成灰土露出白。”这是她对他此生唯一的表白,哀而不伤,只是徒留惆怅。因为他们的爱情从来就不能像江河一样汪洋恣肆,只能像深流的静水,底下暗流汹涌。书中雨波对丽雯说:“你难得一笑,一笑就特别妩媚。是真美,特有回味的美,就像这山这水,刚来时觉得冷酷,处久了竟越看越有滋味,有大美而不言。”
野夫说,在书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经常想到的是同样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沈从文。野夫之文,轻淡恬静,平和有光。他笔下的故事,大都简简单单,没有复杂的结构,蔓生的枝节,甚至都难以归类为小说或散文。然而就是这样的简单,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经过岁月锻造和沉淀过的语言,一字一句,都直击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讲故事是一门手艺,而野夫也想成为这么一个讲得一手好故事的手艺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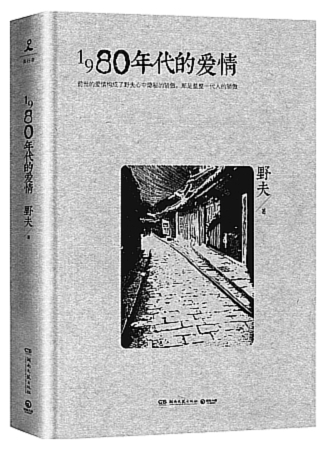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