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所述,是有关一条流传甚广而又众说纷纭的史料,这便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所谓慈禧太后将钓鱼列屿“赏给盛宣怀为产业”的诏谕(见图)。
这件诏书始见于1972年出版的台湾《中外杂志》第十一卷第一期。笔者是从当年2月15日出版的《学粹杂志》第十四卷第二期上,读到沙见林氏所撰《慈禧太后诏谕与钓鱼岛主权》一文。诏书全文为:
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世设药局,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
据介绍:
此诏谕原件是棕红色布料,长约五十九公分(二十三点二英寸),宽约三十一公分(十二点二英寸),上方正中印有“慈禧皇太后之宝”玉玺,朱色,四方形,每边为十一公分(四点四英寸);在“慈谕太常”四字上,盖有慈禧皇太后“御赏”腰章,朱色,椭圆形,高七点三公分(二点八英寸),中部宽四点八公分(一点八英寸)。
1972年初夏,我因涉猎钓鱼列屿问题,回到南开母校求教于郑毅生(天挺)师。郑老仔细看了诏书复印件之后,当即提出了几点看法:
一是材质不合一般上谕:在他所接触的清代上谕中,均为普通白折纸写就,向来没有用棕红色布料书写的。
二是书写习惯不符:光绪时代,如系光绪帝根据皇太后旨意发布的诏谕,写作“朕钦奉圣母(或‘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如系由皇太后直接发布,当作“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三是“慈禧皇太后”大印,有异于清廷一般诏谕上所用玉玺,后者为满、汉文具列,即印框右行为汉字篆文,左行为满文。
四是“御赏”腰章不用于“‘赏’赐”,而用于对书画等艺术品的“鉴‘赏’”。
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笔者细绎了盛氏之子盛恩颐(泽臣)给其女盛毓真(徐逸)信中一段话:
清太医院隶属于太常寺,杏荪(宣怀字)公以广仁堂之关系,蒙西太后恩赏太常寺正衔,太常寺正为太常寺之属官,其时杏荪公本职已为头品顶戴直隶海关道并津海关监督出使大臣,官阶远高于太常寺正矣!
感到疑点颇多。按清代“太常寺之属官”,有“寺丞”而无“寺正”,倘说盛恩颐不谙清代职官而误释(如盛宣怀1892年补天津海关道,绝对够不上“本职已为头品顶戴”),则这一诏谕本身所写“太常寺正卿”就颇为蹊跷:因为太常寺的正职首长称“卿”而不称“正卿”——犹之乎今日部级正职称为“部长”而非“正部长”;诏谕中所谓“该卿”尤属荒唐。
《清史稿·盛宣怀列传》对这一时段的经历写得含混不清:
[光绪十八年]沪上织布局厂定,宣怀筹设华盛总厂复任,弥汉冶铁厂亏耗。于是[张]之洞赏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擢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入觐,奏言筑路与练兵、理财、育才互为用,并请开银行,设达成馆。称旨,补太常寺少卿。与比订贷款草约。二十四年……
这里所记提及,盛氏仅在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间,曾经“补太常寺少卿”。究竟是在哪一年?且看盛氏本人的记载。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为补太常寺少卿谢恩折》中云:
本月十二日行抵天津,与直隶总督王文韶面商诸务。正拟附轮赴沪,恭阅邸抄:本月二十四日,奉朱笔:“宣盛宣怀补授太常寺少卿。钦此。”臣猥以庸愚渥蒙圣眷,方京曹之忝列,愧薄职之弗胜。
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对照《爵秩全览·太常寺衙门》得知,光绪十九年太常寺的主管官员为:
经筵讲官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事务宗室 昆 冈
太常寺卿宗室 溥 善
太常寺卿稽查右翼觉罗 李端遇
太常寺少卿 常 明
太常寺少卿 沈恩嘉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中,仅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太常寺题本中,才出现盛宣怀其名,并且注明“未到任”三字,与上引盛氏自述完全吻合。新世纪伊始,第一历史档案馆丁进军、方裕谨先生已撰文辨明此谕旨为伪。
近年从网页上得悉,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夏东元教授,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数百袋“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钓鱼岛有关的任何资料。他们当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此“手谕”是假的,主要依据是上面的日期和称呼与盛宣怀当时的头衔不符。
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当光绪十九年时,盛宣怀既非“太常寺正”,亦非太常寺少卿,更不是所谓“太常寺正卿”——须知,其时太常寺卿、少卿定额为满、汉各一员,是绝对不能“超编”的。倘在这种褒奖臣工的诏谕内,竟然把对方的职务错写得如此不伦不类,也是旷古未有的奇闻。
拙著1994年本问世后,承香港城市大学雷競璇先生赐寄高伯雨先生1974年初稿、1990年修改的《钓鱼台岛属盛宣怀?》一文,以洋洋洒洒的14页篇幅,从秦汉后无封土赐予臣僚谈起,到对诏书本身的诸多硬伤详细考辨其伪,并且举出了盛氏后人的佐证:
从前有个朋友对我说,徐逸(即盛毓真)的哥哥在日本东京开设酒楼,他听说徐逸手上有这样的一件“诏书”,笑不可抑,他说:据他所知,当时的太监向盛宣怀敲诈一笔钱,曾派人对盛宣怀说,太后打算以某地赐给他为食邑,如果他要此事成功,就要拿出若干银两来打点。盛答,待见过诏书之后才拿钱出来,现在只能先付五千两,送给他们喝点酒。不久后,有太监拿了诏书给盛宣怀看,盛知道是假传圣旨,就没有答应了。据说,这是在日本的盛毓度所说的。
能够盗用宫中印章而又在“诏谕”内闹出偌大笑话者,非太监们莫属!
从另一方面看,太监利用钓鱼台、黄尾屿、赤屿造假,足以证明钓鱼列屿归属清廷,连宫内太监也熟知。诏谕虽系伪作,但盛氏广生堂药号长期曾在钓鱼屿采集药材,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不但是一种以采集生草药(而后用以制成药丸)的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此与台湾许多渔民每年前往钓鱼台四周中国固有领海捕鱼,同等重要。采药与捕鱼这两种合法地使用钓鱼台及其领海,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地理意义与政治意义”。也就是说,迄于甲午战争爆发前9个月,中国仍在钓鱼列屿海域和平地行使着主权。
中国史家继承了秉笔直书即“实录”的优良传统——“实录”者何?班固等学者道:“(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学者有勇气排除虽有利于己论但经不住推敲的个别史料,有信心认定此举丝毫无损于钓鱼列屿之为中国领土的结论。
(摘自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略有删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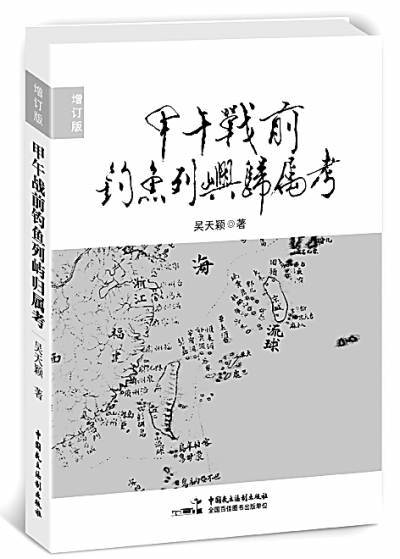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