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我由沈阳飞往喀什。原本6小时的航程,却意外地拖长到18小时。这让我倍感远足南疆的不易。能到帕米尔高原是我年轻时的梦想,而能在这样充满传奇的高原上聆听一场交响音乐会,则更添神奇诱惑。
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不过200公里路程,却因修路多次绕弯缓行。314国道上,满载深圳交响乐团演奏员的大巴如同一条酒意微醺的大鱼,摇首摆尾。沿途无尽的雪山冰峰,层层峥嵘,奇妙风光影像般在车窗外晃动,如梦似幻。年轻的乐手们忘记了连日的演出疲惫,在晃动的车厢内挣扎着举起各自的手机或相机,对着窗外一阵拍。
喀什是深圳的援建城市,贫困而奇异的风情之城不仅需要大量的物质援助,更需要丰沛的精神资源。此番万里之行,将深圳的交响乐“好声音”带到了这里。原定的两场“喀什噶尔之夜”专场音乐会,竟因观众澎湃的爆棚而追加一场。然而,观众的反应仍然如河流般一路相随,随队的文化局领导在路上接到了一条条来自喀什观众的短信:“你们在喀什的演出大家都说震撼。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强烈希望明年还要来!这是喀什干部群众的呼声!”
带着被拥戴的喜悦与被赞美的温馨,深交一路豪情地驶往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部、喀喇昆仑山北部,得天独厚地享用了慕士塔格峰山脚下的一方神奇土地。这里的阿拉尔金草滩比黄河源的星宿海更让我感到神奇和优美。草滩中有清亮的泉水,夜幕垂临时,这些泉眼如遍地的星光。草滩间有白色毡包,如同砍削好的椰子排列,偶有炊烟飘散,为黄昏增添了一抹生动的人间烟火韵味。
深圳交响乐团的舞台就搭在这里,无比的空旷豪放,比柏林的森林音乐会的舞台更大,更辽阔。喀喇昆仑山脉是舞台依托的遥远而巨大的后台衬幕,那山体肌肤的沟痕如同长幕的间褶,均匀地排列着夜色的庄严。而阿拉尔金草滩坦荡开怀,在落日下蓄满深情。今夜,交响乐能够在这里奏响,怎能不让人亢奋!
观众早早坐满了座位,更多人却站着。然而,再多的观众在这样空旷的高原上仍不显得拥挤。22点,古石头城那边的天际与草滩同时被巨大的黑幕覆盖,这才开始了演出。然而,风却趁机愈刮愈烈,气温突降,让人领略到“晚穿棉袄午穿纱”的冰山帕米尔气候。
董蒙、许莹、秦懿和林译姝的弦乐四重奏组合,去年代表中国应邀出访波兰,参加“马耳他”国际艺术节,让中国作品大放光芒。然而,有着丰富演奏经验的四重奏,却想不到在帕米尔高原一出场,就遭遇了降温与山风的考验。舞台正中横空拉起的《帕米尔之声——深圳交响乐团塔县慰问演出音乐会》条幅,被山风刮得猎猎作响。她们的裙带与额发飞扬起来,身子几乎无法坐稳,谱架更是险些被刮倒。
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以其独有的颤音,通过高架的音箱播撒向无限的空间,但是,琴音仍然盖不住风声。乐音与风声协奏着,相融着,产生了奇特效果,那是一种失真的颤音,也是一种激动的声波。它们撞向昆仑山脉深黑的山体,飘向更高一层如清月挥洒的冰峰雪顶。哈萨克民歌改编的《玛依拉》、聂耳作曲的《金蛇狂舞》、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一杯美酒》等旋律,在这个夜晚随风呼啸,而后如烟般散落在大草滩的寂寞深处。演奏下来,女孩子们的手都冻僵冻麻了。
在这样巨大的场地演出室内乐四重奏,已经难为了选手,然而更有胆气的是独奏的张雷先生。这位身材更为单薄的小提琴手从小就喜欢耀中作曲、盛中国演奏的《新疆之春》,几十年来带着它走遍美国,每每受到听众欢迎。然而,这一次演奏是他平生最为自豪的一次,因为在猛烈晚风的陪伴下,他将积蓄几十年的内心情怀,播撒在辽阔的帕米尔高原上。尽管他被风刮歪了身子,只能侧对着观众席,但他力保稳住琴,把住位,不让弦音走失。这是一次冒险,更是一次磨炼!
铜管五重奏体现了乐团的管乐实力。《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康定情歌》《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均为中外名曲,五位男子汉劲鼓腮肌与强风搏击,将声音吹到极致。这是男子汉的呐喊,是大胸腔迸发的声音,这个声音令人联想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帕米尔嘹亮豪放的歌声,还有冬不拉的节奏!
如果说,在这样的劲风中完成管乐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后来乐手们在海拔5000米的红其拉甫边防哨所的演出,更加令人怦然心动。
衣丞在国内属大师级的演奏家,而他在哨所面对三位战士吹奏《说句心里话》,却异常艰苦,甚至有几处断续。他脖筋暴鼓,像完成登顶雪峰一样完成了最后一句,大喘着退场,步履踉跄险些跌倒。而马俊吹奏的小号《送战友》,让战士们泪眼婆娑。最后,为哨所拉起《梁祝》的秦怡、林译姝更让战士感动。这两位以柔克刚的纤弱女性将琴弦渐次推深,《梁祝》的旋律在深沉中散发出浓郁的味道,此前坐姿一直威武硬朗的战士顿时松弛了下来。有谁知道,这两位小提琴演奏员因高原反应,一整天粒米未进,靠药物支撑才脸色煞白地完成了这场特殊的演奏。
这绝对是一次特殊的演出。这些80后的年轻人,不曾看过《冰山上的来客》,也不曾体会过失去战友阿米尔的那冰川震裂的歌声,然而,他们以自己的音乐,让哨所战士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至于冷峻钢硬的帕米尔,历来不缺音乐,不缺歌舞,不缺鹰隼文化。但是,对于深圳交响乐团送上门的这种温柔纤细的“雅奏”,大概也是头一次领教吧。(作者为报告文学家,《鸭绿江》原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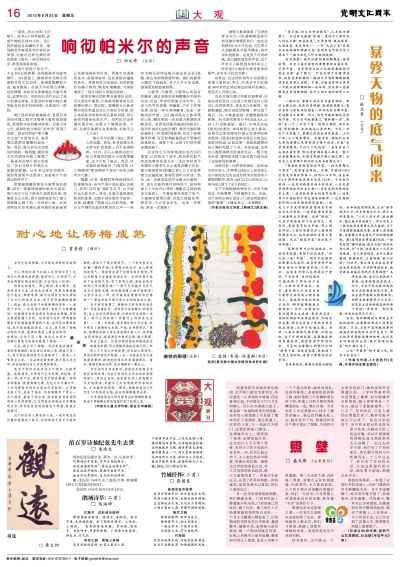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