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间的北屋,向阳。东边那间安静,住母亲,西边那间住夫人。纵是像人们说的,夫妻两个从早到晚几乎不说一句话,但中间这间,一家人吃饭时总能在一处坐一坐。
推开红漆木门,屋子里还有浓浓的南方樟木的气味。母亲带不过来南方,就搬来藤柜藤椅,好在接着地气,藤不会开裂。吱—吱,藤床响动一下,母亲在翻身。两个女人就这样起居在先生的身边,这大约叫他稳妥。
先生呢,在三间北屋后接盖一间小屋,又睡觉又当书屋,北京人叫“老虎尾巴”。为什么要叫这么硬生生的名字呢?先生叫它“绿林书屋”。书屋窄小,只放一张两条长凳搭的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屋窄小,但窗户宽敞,他还亲自买了大块的玻璃安上,小小的屋就有了大而亮的眼睛,能透过玻璃看到后院的榆叶梅、青杨,甚至院墙外的两棵枣树。冬天,树木落尽了叶子,坐在书屋里,还能看到夜空。北屋老式的木格窗也镶上了玻璃,前前后后都透亮了。坐在书屋里,前院的白丁香、碧桃,隔了玻璃,千眼照花;花儿开时,前屋后屋也都香了。
三开间的南屋放书柜当会客厅。西侧小小的一角,一扇木门关住了所有凌乱的杂物。
先生借钱买来这个废圮破败的小院,亲手设计,后来,它就这样蓊蓊郁郁了起来。
80多年过去了。那一天,站在安静的院里,只听见树叶颤动的声音。
我想起,先生在这小院里的两年多是他一生里最为彷徨不平静的时候。隔了书屋玻璃看,书桌上方有一幅速写,先生喜欢的一幅画,依然是满纸的不安宁。两年多,先生在油灯下,写了《野草》、《华盖集》,还有《华盖集续编》、《彷徨》、《朝花夕拾》、《坟》里的部分篇章。大部分文字幽暗诡谲,有着那个时代沉沉的影子。
油灯亮了,夜虫撞在玻璃上叮叮地响。鬼眨眼似的天高而奇怪,哇——夜游的恶鸟飞过去了,墙外的枣树像铁丝一样刺向天空……
人们于是都要找先生屋后院墙外的枣树看一看,但那两棵已经死了。旁处的一棵枣树不是先生所写的两棵中的一棵,它还茂盛着,但树皮沧桑,结满了厚厚的痂。
于先生言,这个小院里总有些温暖。他在书屋里写了很多信,在柔软的宣纸上,他称那个比他小18岁的女孩子“兄”,后来,又亲爱地唤她“害马”、“小刺猬”。满脸倔强髭须的大先生,唇齿间也会发出这样柔情的声息。
先生之后去了南方,留下了四合小院和两个女人。先生亲手种的白丁香、榆叶梅一年年长大,院子里的两个女人一年年老去。最后,就剩了那个不会说北京话的大夫人,在这个小院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我想,于这个四合小院与那个南方女人来说,几十年间经历了太多希冀、受伤、失落。
那天,守护院子的人说,每年初春,丁香开时,满枝繁花,清香四溢。
先时,大夫人可在一院子的花香里想着南方?
(作者为作家、编辑,著有散文集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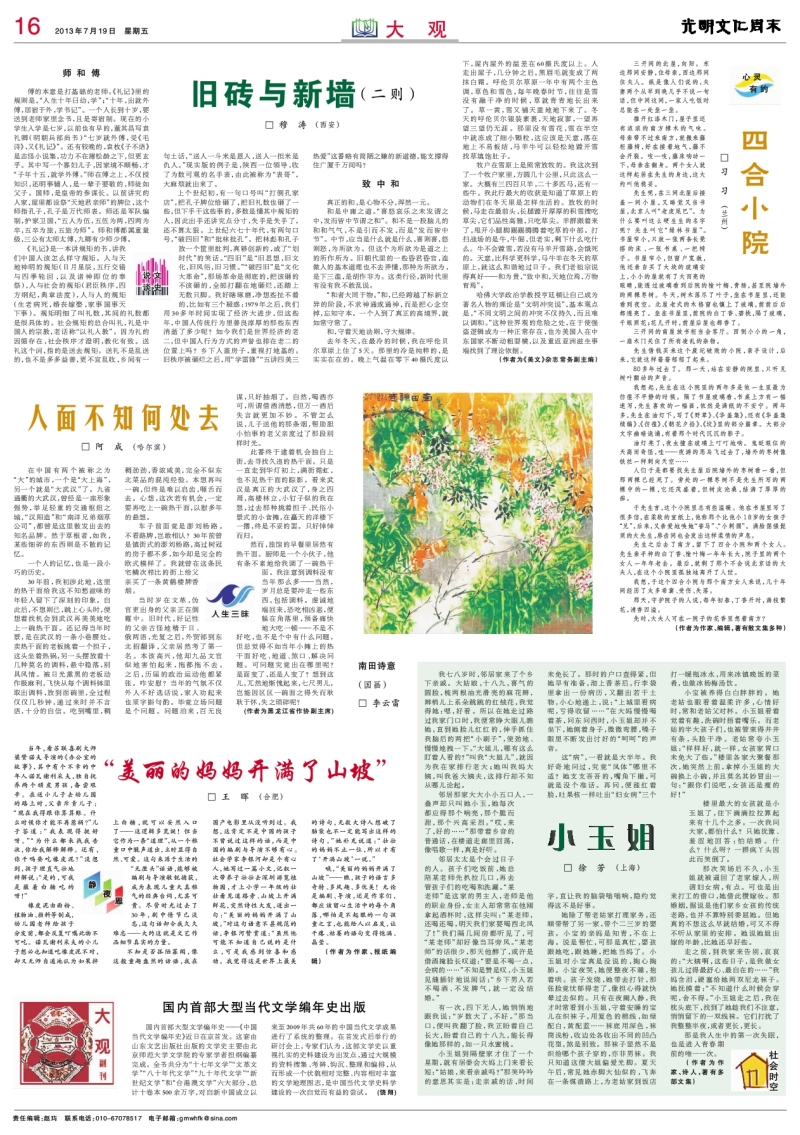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