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片”:“闻字作家”“中国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志愿者”“区残联副主席”。
他创造了不少“第一”“唯一”:国内第一部由盲人创作的历史长篇小说、举办全国首个盲人书法家作品展、北京市唯一一位盲人监狱思想辅导员。
他身上还有着不少独有的特征:0.01的视力、不到一米五的身高、特殊的养子身世。
他就是盲人作家张骥良。他真像一本厚实的书,里面有着数不清的故事,叫人咂摸起来时而欢笑,时而忐忑,时而感动,时而沉思。
从纵横交错的文字里找到了认可
1954年,张骥良出生在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夜晚。同样在那个夜晚,一对夫妻从北京一家医院附近的小纸箱里将他捡了回家。为了养活这个捡来的小男孩,已有身孕的母亲做掉了肚子里的亲骨肉。雪上加霜的是,一个月之后,病魔永久地夺走了小骥良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或许因为自己是一个残疾孩子的缘故,小时候的张骥良内心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自卑和感伤。在无数个茫茫的黑夜中,他唯有靠着0.01的视力埋头于书本。二年级时,张骥良写了一首名叫《太阳和我们一起做早操》的小诗。写完后他拿去寄,由于个矮够不着邮筒,就找来两块砖头踮着脚,就这样把诗投了出去。随后这首诗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张骥良也被称为“校园小诗人”。这首现在被张骥良笑称很“幼稚”的诗在当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和鼓励,也在小骥良的心里埋下了写作的种子。
中学毕业后的张骥良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即便是上班,不管多忙、多累、多苦,他都不间断地坚持码字,那纵横交错的方格字仿佛成了跳动的音符,陪伴着他走过漫长的黑夜。起初,他走得并不顺利,写了上百篇稿子,屡屡被退稿。张骥良不甘心,收到一封封退稿信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抚平、装订,然后在退稿单的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终于,他站在失败的废墟上又一次赢得了成功。1977年夏,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的十几年中,他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还加入了北京作协,成了京城小有名气的作家。
命运再一次跟张骥良开了个玩笑。1994年秋,张骥良下岗。每月300元生活费,让整个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如何养家糊口?当时的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寻挣钱的机会。一次与作家叶永烈的偶然谈话,让他决定转向名人访谈写作。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他已跑了100多家单位求职,磨破了好几双鞋。时至今日张骥良并不否认当初之所以改写名人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只能背水一战。”
写名人并不容易,首先寻找采访对象就是个大问题,此外一没记者证二没正式单位的窘状更是增加了采访的难度。为此他特别感谢当时身边的朋友,吴祖光、冰心、贺敬之等文艺界的人物纷纷主动给他介绍采访对象。他清晰地记得自己采访的第一位名人是当时还在主持《正大综艺》的杨澜,他说“杨澜是给自己机会的人”。就这样,他采访过的名人记录一次次被刷新着,艾青、王光美、巩俐、张国荣、梅艳芳、施瓦辛格……无论采访对象是出于同情、好奇还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考虑来接受自己的采访,张骥良都坚持下来了,粗略地算下来他一共采访了600多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光名人访谈和纪实作品就发表了250余万字。
2008年1月,张骥良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溥仪 终结一个时代的人》付梓,一经问世便引来了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关注。而在这背后,却凝结着张骥良数不清的心血。为力求书稿内容的客观真实,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搜集资料素材,先后阅读七八百本相关书籍,采访历时二十余年,走访人物百余位,建立三万多张资料卡,整理采访录音四百多盘,最终历时十四个月完成三十多万字的书稿。
“做调查记者是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
1997年底,张骥良被《北京社会报》聘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负责一个副刊。彼时,他已经43岁。他开始把视野投向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
为了采写都市乞丐群体的生存现状,他向老母亲借来一件破布衣裳,又往脸上抹了点锅黑和泥巴,跑到火车站蹲了四天三夜,兜里没有一分钱,他跟着别人吃剩饭剩菜,住街上的水泥管子,喝地沟里的脏水,真真实实地当了一回乞丐。当他饥渴难耐,嗓子冒烟地面对路人喊出:“大爷大娘行行好,给一口半口吃的”;当他第一次把人家吃剩下的半块馒头捡起放入口中;当他为了探清丐帮内幕,第一次下跪给师傅磕头……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凝成了有血有肉的文字报道。文章见报后,公安、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对丐帮群落进行了一次大的清理,安定了社会秩序。
2002年夏,他从一个朋友那听说京郊有一伙“血头血霸”,专门找人来代替一些单位职工献血,并从这些单位中吃拿回扣。“当时一些单位有献血指标,但员工不肯献,只能找人来代替。” 张骥良回忆,“代替献血的人多为外地人,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费用。”为了查清这个问题,他以眼睛看不见、没工作需要卖血为由,只身一人找到卖血者的住处,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七天七夜,终于摸清了整个交易背后的“黑幕”。
“那些卖血者为了稀释血液,经常吃烟灰,我也跟着他们吃,烟灰卡在喉咙里,甭提多难受了……”回想起这些,张骥良感慨不已,却不后悔自己的经历。后来他写的《京城流浪的造血机器》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经多家媒体转载,那些弄虚作假的血站和找人代替献血的单位也受到了审查。
做调查记者,张骥良时常遇到各种危险,暗访发票交易黑幕被人暴打、探访丐帮惹怒头目扬言要悬赏抓来挖他双眼……这些听起来令人生畏的生死经历写满了张骥良的记者生涯。“我端一天记者这个饭碗,就要说一天实话,每一次我都会把我采访到的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也不唱高调,我没有为人民代言这么高的想法,但是对于我,就是要做一个说实话的记者!”张骥良感慨。
张骥良写下的报道并不总是能让所有人为之喝彩,相反有时伴随而来的是委屈、无奈和官司。一对捡破烂的夫妇在垃圾堆里捡了五个女婴,夫妻俩省吃俭用,把五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张骥良据此采写的报道发表后,被数十家媒体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可没想到,那对夫妇所在乡的一位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认为他的报道为乡里计生工作抹了黑,说“如果别人读了这篇报道,把孩子都往我们乡扔,我们怎么办”,并将他告上法庭,最后张骥良不得不写书面检查。
“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所以做调查采访也算是我的一个优势吧。”张骥良坦然地回答。有人说张骥良为了图名图利,把死都忘了。他说,“其实这就是一个盲人记者的边缘人生和边缘采访。”
“帮助残疾人,只想尽可能地接近光明”
张骥良靠着文字赢得了名气,靠着写作赢得了成功,而在收获这些名与利的同时,他内心格外清楚,只有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这些名利才会有它们真正的价值。身为北京市残联主席团委员、朝阳区残联副主席、盲人协会主席的张骥良始终忙碌着,他不断地为残疾人公益事业而奔走,为残疾人的权益鼓与呼。
一次,团结湖社区的一位盲人去医院看病,到医院后被一个热心的自称为医院工作人员的人领着跑上跑下地去办理各种手续。当“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之后”,来到医生面前时才发现被骗了。领着他跑来跑去的“工作人员”竟然是个骗子,骗走了他身上带着的六千多元钱。欲哭无泪的盲人朋友只好拨通了张骥良的电话向他求助。听完对方的诉说后,张骥良二话没说急忙赶到了医院。详细了解事件经过后,带着那位盲人去找院方。“医院没有设置导医从而导致盲人患者被骗,医院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张骥良据理力争。但对于张骥良的要求,院方却毫不理会。跟院方沟通无果后,张骥良想到依靠媒体的力量来帮忙。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一家知名媒体记者的电话,跟对方说明了情况之后,他又开始拨另一个电话。这架势让医院着了急,最终决定赔偿盲人患者一半的损失。
有盲人朋友跟张骥良反映,说人家明眼人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但咱盲人朋友就不行,只能听到奏国歌。张骥良犯了难,寻思着盲人怎么看升国旗啊。他转念一想,既然看不着,为什么不能摸摸国旗呢?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国旗护卫队格外忙碌,张骥良通过联系,反复和武警十四支队协调,最终实现盲人朋友的心愿。当第一面国旗拿来的时候,盲人朋友很自然地把脸贴了上去,泪水早已在眼眶里打转。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可以如此零距离地亲吻国旗,用指尖去感受升旗仪式。
张骥良还是北京市唯一一位盲人监狱思想道德辅导员。受聘之后,他先后数十次走进延庆监狱,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叫赵海潮的盲人服刑人员。当时的赵海潮心灰意冷,对未来没有一点希望。张骥良不断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并亲自给他送去了盲人专用的写字板、盲笔,还鼓励他将按摩作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又四处寻找按摩书籍,将录好的按摩教学磁带,一并送到了赵海潮的手里。捧着这些送来的物品,赵海潮不禁热泪盈眶。后来赵海潮因在监狱表现优异,减刑提前出狱,他拉着张骥良的手说:“是您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
张骥良说:“我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只想用自己通过写作赚的这点名分,多帮助一些残疾人朋友,尽可能地接近光明”。(本报通讯员 周 青)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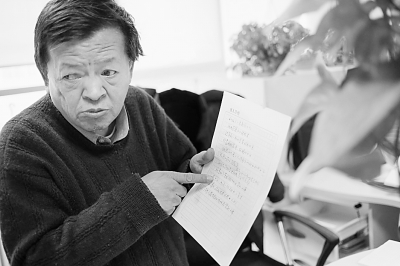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