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雪霁,乍暖还寒。法国友丰出版社社长,初春在北京获得“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荣耀的潘立辉先生邀我和妻子董纯在拉丁区一餐厅会见法国女作家卡特琳·文慕贝,彼此相识甚欢。文慕贝女士谈锋颇健,一落座就倾吐起她对中国的热烈情愫,几乎无暇动侍者端上来的可口菜肴。她的畅销小说《爱米莉·爪哇,1904》中译本于2008年5月在北京由作家出版社印行;另一部纪实作品《每一个人的中国》今年3月中也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我来赴约前抽空看了这两部书,尤其是《每个人的中国》,描述了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中国,读起来感觉分外亲切。
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凭着西方政治家罕有的胆识承认新中国,中法建交。文慕贝应中国妇联邀请访华。期时,她刚在巴黎出版了《怪诞的美国》一书,向世人揭示了大西洋彼岸一个种族主义的扭曲社会,因而渴望在中国发现真正的“新世界”,启开莱维·斯特劳斯语汇里那个“装着各种梦幻般预示的魔盒”。她出席了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的开馆仪式,与最先来京拓展中法关系的年轻法国外交官兼汉学家马克·孟毅邂逅,由“中国缘”结为夫妻,从此为促进法中两国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效力。
其实,文慕贝的“中国情结”早在她的小说《爱米莉·爪哇,1904》里就有过充分的流露。那部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爱米莉形象是依照她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塑造的。20世纪初,波尔多姑娘爱米莉远赴印尼爪哇岛的巴塔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在那边接触到义和团遭镇压后流亡岛上的一群中国青年,还见到了到当地寻求华人侨社支持,回国搞变法的康有为。爱米莉遇见一个中国热血女青年“佩”,二人亲如姊妹,一起参加了爪哇人民反抗荷兰野蛮殖民统治的斗争,并跟进行地下活动的土著勇士阿南多成为情侣。在后者被逮捕流放时,痛不欲生,对自己的法国丈夫吕西安心生恶感,视欧洲殖民主义分子为“压迫者”。
中国旧话本小说里常常提到“爪洼国”,指的是一个遥远的“乌有之乡”,而文慕贝小说里的“爪哇”却离中国大陆不远,岛上有一个“华人世界”,常听到谈论谭嗣同、秋瑾、黄兴,从而催生了她的“中国情结”和追求友爱的崇高意想。在小说的“尾声”里,读者听到女主人公决心要跟着“佩”一起乘船渡海去中国,“走向另一种命运”。
文慕贝终于实现了她的宿愿,来到了新中国,到北京的当天就站到了“十一”国庆的观礼台上,看见了一个东方巨人苏醒过来,满怀激情奔向未来的宏伟场面。她走下观礼台,加入节日欢乐的人群,进北京的胡同里拜访普通中国家庭,广交朋友。接着,她乘火车漫游山东,再“南下!南下!”至上海、广州,欣悦地瞧着中国老百姓一张张“温柔”的面容,为东方异国的“万花筒”目眩。大文豪巴尔扎克早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在他的《人间戏剧》里预言,到达中国的人会“获得新生”。而文慕贝实践了巴氏的“中国梦”。整个旅途,她都沉浸于一种亢奋的心境,至纫中国人的高谊,乃至经香港返回巴黎时,对中国顿生一股异样的“乡愁”。
在《每个人的中国》一书里,作者深切感到中国“是一个谦恭的民族”,“暖水瓶”象征着中国普通人的气质,远不像一些西方人那般虚妄和狂傲。书中有一个章节“欧洲人在北京”,就描绘了一些住高级饭店的西欧人心态,说他们在华患了“精神病”,逢人就搬出自己对中国抱着偏见的陈词滥调,似乎“中国人全都在准备生吞活剥地吃掉他们”。她提到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就对这种现象忿忿不平,奉劝当时访华的法国作家茹尔·鲁瓦放弃西方人在东方人面前显露的优越感。
在这次巴黎拉丁区的会晤中,文慕贝表达了自己对全球化中一种旅游畸形发展的独特见解。她曾在亚太地区生活过20多年,足迹遍布印尼、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和瓦努阿图,发现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有随时势和“民主化”消遁,而以“新殖民主义”形式绵延。一些旅游实质上形成外来买方与当地卖方的交易,特别是一些西方人的性旅游,令人作呕。她的看法里显然包含着那种对现代文明和超消费社会的质疑。
文慕贝是作为法国新闻界的自由撰稿人最早到中国进行系列采访的。她以客观的笔触在《每个人的中国》里报道了上世纪60年代的“新中国”。她也是少有的在文革初期跻身天安门广场红卫兵人潮里的法国记者。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尚不能预知祸之将至的懵懂时刻,她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动荡。然而,事过之后,她认为“十年浩劫”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个过程中遭受的“挫折”和“阵痛”,不应该因为难免的历史反复而气馁,更不容西方借此否定一切,将一个伟大民族苦难而又辉煌的奋斗历史抹得一团漆黑。法国一些媒体现在大搞“舆论一律”,不遗余力地歪曲现实,对中国竭尽污蔑之能事,有失新闻职业道德,至少也是出于“愚昧无知”。有人摆出教师爷的架势,动辄要“干预”,实为自不量力,不得人心。这番言谈让人想到她在《每个人的中国》这部纪实作品里所表达的“用欧洲的法律和神话来解释中国红色政治社会是不可能的。一切对现代中国精神的取笑和攻击都会一败涂地”。
到二十一世纪,文慕贝和她的夫婿孟毅又数度访华,看见“梦幻般的变化”,也留意到北京的雾霾,不无抱憾。半个世纪前,她在《每个人的中国》里“新中国的蓝天”一章中就曾预言:“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这里发奋建设,新的建筑迅速出现,老北京就不复存在了。低租金住房将代替胡同,人们会砍掉垂柳以腾出更多的空间……经历那么多年的艰难困苦之后,他们会奔向这种所谓‘先进’文明之快乐、舒适,打破禁忌。这种文明,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美国式的,明天将成为欧洲式的。中国会不会找到另一条道路,奔向另一个目标呢……”
初次跟法国女作家文慕贝接触,再细读她的作品,我发现她身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以大观思维,想历史地、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为此,她找到了我1985年在巴黎出版的长篇纪实小说《延安的孩子》,还为夫婿孟毅觅到了中文版《悬崖百合》,二人同时阅读两种不同文字版本,然后来信写道:“您追述了一个时期的中国英雄史诗,动人心弦,也让我们俩感受到了温暖的人情……”(沈大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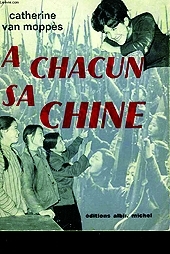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