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侯健飞的《回鹿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我被那发自内心的、毫无修饰的文字所打动。
侯健飞的写作直接来自父亲的召唤:“天堂里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父亲的眼睛。”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之后,侯健飞才慢慢觉悟到父亲是上帝派到他身边的牧师:“随着往事的复活,我逐渐产生一种隐痛般的愧疚感,觉得自己很失孝道,既没有好好珍惜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也没有好好爱过父亲一回。”于是他以一种忏悔的姿态来回忆他与父亲的交往,他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爱。
从侯健飞的叙述中,可以发现,一切错愕都缘于有两个父亲在他的心中打架,一个是血缘上的父亲,一个是被社会化的父亲。
台湾研究儒学的著名学者林安梧曾论述过父亲在中国传统伦理社会中的意义:“‘父’不只是作为‘子’的自然生命的来源而已,而且它亦是文化生命乃至价值生命的来源。”父亲的意义在革命文化中得到了延伸,我们从小接受教育,要继承父辈们开创的革命传统,一个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父辈形象铭记在脑海中。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侯健飞,脑海中也有了这样一位被社会化的父亲形象,他以此为楷模比照自己的父亲,便对父亲的平庸、潦倒深为不满,于是“俄狄浦斯情结”在侯健飞的少年时代就表现得特别激烈,长期以来他以一种冷漠和对抗的态度与父亲相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父亲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父亲仿佛洞悉了儿子的一切,并不在意儿子的态度,默默地帮扶着儿子成长。
侯健飞记述他在姐姐琴死后一段时间里特别恐惧却又不愿表白,只有父亲了解儿子的心理,会在夜晚及时拉亮电灯,对儿子说:“我出去尿尿,你去吗?”就是这一细微的行为,让侯健飞“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于我的重要性”。事实上,父亲也曾有过戎马杀敌的辉煌经历,但他从来不炫耀这些,因为他不过是在尽一份职责,他不会去为了做“社会化的父亲”而活着。这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父亲的伟大之处。也只有在岁月的磨砺下,父亲的伟大才会一点点地显露出来。面对父亲的伟大,侯健飞痛心地说:“原谅我,就让岁月的鞭子来惩罚我的自私和不孝吧!”大凡一个人带着忏悔之心去思考人生时,都会获得这种具有警示般的发现。
除了父亲之外,侯健飞还写到了众多的亲人、邻居以及童年的伙伴。他丝毫不隐瞒他对他们的过错,也不隐瞒他人在交往中的过错。但重要的是,大家相互帮衬着走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回首望去,侯健飞感慨道:“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兄弟关系,还是亲戚关系,都是能通过关爱和善意改善的,否则,宗亲关系不会有如此大的社会要基,人类文明更不可能延续和发展。”
中国有一种避讳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传记和自传的写作中得到充分的表现,隐恶扬善似乎成为这类写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很难读到像《回鹿山》这样坦率的自传性作品。从这个角度说,西方的“忏悔录”式的自传传统真应该好好地加以推广。侯健飞写作《回鹿山》,就像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投入了一块明矾,它让混浊的水逐渐变得澄清。《回鹿山》表明,传记和自传的写作应该成为一次净化心灵的“忏悔录”。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忏悔录”,这个喧嚣的时代也就多一些澄明和安宁。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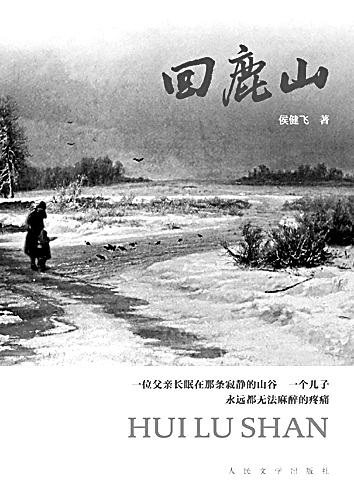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