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为人知的楷模,被一代代社会成员精神化了的公众形象,他的理念、言行长期作为正面价值标尺,人已故去五十年,但他晨阳般青春的脸庞仍为亿万人所熟悉。这就是雷锋。人们对他的了解和认识因为已经固定化而显得故事几乎完备,所以,偏好新鲜故事的人更在意考掘他的瑕疵和平常——这样的人物要作为主人公进入长篇小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作品必须做到,在固然可敬之外留下更加感性可亲的印象,令读者更加珍视他在人生意义、公共交往和日常生活中综合的精神榜样作用,以不朽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因而作家必须在尊重公众共识和还原主人公成长细节上找到艺术地重塑雷锋的叙述方式。同时,作为小说,必须使小说文体得到足够的尊重,至少不能让文体受损,因为主旨上创作者认同的激情过当,读者接受的自主性就容易被压抑,宣教的意味一旦凸显,就容易使作品近于抒情散文、特写、报告或演讲;而太重视日常和过度虚构“你所不知道的故事”,则会使作品流于媚俗,其感染力、真切度和审美的品质就大打折扣,有失雅正的文学格调。这样的作品,如果想要留下来传下去,高远的精神指向、近邻般的人间情味和悠长的文学意蕴都必须兼顾并融。
黄亚洲的长篇小说《雷锋》基本上做到了这些。也许它可以列入习惯上所说的“主旋律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中,以此区别于一般的赶制出来的应时性读物。
以小说的方式赋予雷锋以鲜活的生命,使雷锋经由“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创造成为长久地跃动于读者心中的人物,通过文脉浸润人心,从而让雷锋精神更加牢固地嵌入中国人的人格体系,是《雷锋》总体的艺术追求。
为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小说于外在架构上照顾了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大体上顺应主人公生命历程,进行成长小说式的历时性叙事。优秀的成长小说本身都有普泛的认识功能,几乎都可以让读者视为自己成长的镜像。雷锋的成长年代虽然与现在的青少年有所隔膜,但他底层出生、少年出走、青年磨练并成器的经历,具有一般文学人物所难以具备的励志作用。小说《雷锋》的作者找到了使小说扎得稳、立得住的深层结构,即作为决定雷锋的人格养成和精神生成的基质性趋动力量——亲情。小说与人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这个原发地带辐散开去,加之时代的元素,雷锋与雷锋精神的生成线索和可接受性找到了恰切的支撑体。
也就是说,正是亲情叙事这个内在结构的确立,使千百次重复并逐渐硬化为标本的“雷锋事迹”活化为寄托无尽想象的“雷锋故事”。不幸的童年,先后丧父丧母,旧社会里穷乡亲对自己视同己出的怜悯照顾,决定了他人生底色上的立场选择。那是一种加宽的伦理力量。家乡、工作过的地方、部队里甚至在路上,亲情无时无处不在。在新社会里让他更深地意识到祖国处处有亲人。在工作层面和日常层面,他渴望更珍惜来自组织和人群的亲情。书中布满活泼而扎实的细节,令这一切可感可信。微笑的脸上有灿烂的阳光,因为他有热诚的感恩之心,有朴素纯白的心思,致使他在生活和学习中逐渐养成了对社会的奉献习惯:利他律己、助人为乐、强烈的岗位意识、不竭的劳动激情等。重情入世者超凡脱俗,知恩图报者快乐满足。懂得感恩惜福之人,终被世人不断感念和效法。高尚的雷锋其实是日常亲情中的成长者,在同心相亲的时代,雷锋身上的伦理力量渐渐升华为他所代表的国民精神。
与上述结构设置相关,作品以成长小说的元素,以亲情伦常的情境,尝试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进行再创造。
单纯并不意味着情感就不丰富。在小说中,雷锋是一个立体的人,有理想信念,也有常人对喜怒哀乐的善感;慎独自爱,也与众多亲友为伴相知。长辈和领导之外,作品中的同辈人物群像个个跃然纸上。喜宝这样出身不同的童年伙伴,得到了雷锋悉心帮助而比照着成长,他似乎可以视为受雷锋直接影响的一类人物。战友乔大山相对粗粝的脾气与雷锋细致亲和的秉性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中最出彩的是女性形象,老一辈的九斤大妈自是令人感动的农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几位同辈女子,爱恋雷锋的易华妹妹,朝气蓬勃,又有些小固执小任性;小说中,雷锋的姐姐较多,王姐、岳姐、健姐等,这些女性虽然性格迥异,但都可以视为雷锋成长的见证和雷锋心理上的亲情补偿。作品对雷锋丧母前后用墨较重,对女性形象也是着重刻画,“全国的大妈大娘都是我的亲娘”这样的表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衬出雷锋对母爱的向往。这种适度的文学意义上的心理暗示,让雷锋形象的塑造显得更为真切和丰满。
从庚伢子到雷正兴再到雷锋,三个名字几乎可以代表雷锋成长的三个阶段。伦常中的善与年轻人的真,苦孩子、离家闯荡的少年到阳光大男孩般的青年,他是国家主人、劳动者、军人,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最具光彩的身份,已经足够骄人。天安门前骑摩托照相这一类年轻人偶尔的小小的虚荣心,也本可理解,但分寄照片时,透出了感恩亲情的归属感。爱照相,这也是普通人爱美之心的证明。雷锋的成长,长成了雷锋精神,也是成长者指向“新人”而不是“多余人”的长成路径。其核心价值符码集于一身,传统优秀人品和新时代先锋质素相融合,是充满了向上之美的“社会主义新人”。
小说在资料取舍上很能见出作者艺术上的功力。可以想见,五十年来,雷锋日记、影集、雷锋事迹报道、采访资料等,如此繁多,而国人对主要故事耳熟能详,但是作者依然能够发掘出新的角度、线索和故事,原因就在于作者更注重使人物“活”起来的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变成雷锋作为标兵更作为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以此来激活并还原雷锋的文学生命: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雷锋从何而来、如何成长、怎样长成。
能够看出,小说在语言方面狠下了一番工夫。鲜活的方言,不同人物的不同语气,都尽量展现文学语言的魅力。尽量用对话、描述而不是交代和告诉的方式,让雷锋时刻处在对话关系中。于是雷锋与情境、他人的关系,就显得彼此不可分割。包括雷锋自己的表达,也是有交流的表达,而不是单向的录音。
总而言之,长篇小说《雷锋》是现时代“主旋律文学”的重要收获,作者对“主旋律文学”所作出的辛勤而卓有成效的艺术探索,值得肯定。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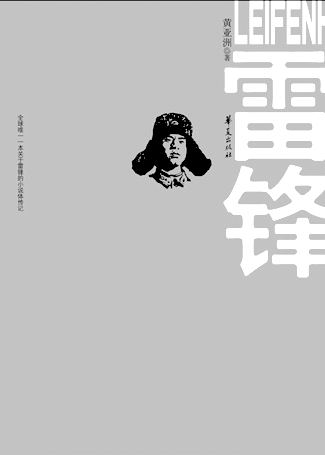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