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先后出了两本书,年初一本,年尾《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相较而言,后一本则更加用心,写了几年。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本还愿之作。而两本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这对于一个只是在尽自己本分写作的人来说,的确是无比幸运的事。
岁尾年关,借助本文我想与读者分享的是我在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的一些心得。
一是做非你不可的事情。每个人的人生都独一无二,每个年龄都有当务之急。有些事情你不做别人可以做,有些事情你不做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做。2008年夏天,在许多人关注奥运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偏远的山村。回到自己的老家做田野调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只有我愿意去做。在奥运与命运之间,我将视线投向我所熟悉的本乡本土,并将此视为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更在于我的经验、我的回忆、我的视角,甚至包括我对一个村庄的热情都无人可替。
二是不要丢掉自己的语言。我一直强调,寻找一种适合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迷恋诗歌,但到后来读完大学,我几乎放弃了诗歌,因为诗歌不足以表达我自己。同样的原因,两年前我停写了许多专栏。《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我写作上的尝试,即我所谓的“三通”,包括时间上打通(不只是写三十年来的农村,同样回溯过去六十年与百余年来的中国农村变化),空间上打通(不仅着眼于一个村庄,同样由村庄拓展到中国,也包括我对欧洲农村的观察),此外是理性与心灵的打通,即我说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虽然我也从事学术研究,但我没有必要强迫自己接受那些湮灭文字个性与语言之美的“学术表达”。我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我不能为了学术而丢掉自己的语言。
三是要有眼力也要有脚力。所谓“眼力”是指对时代走向有一个整体判断,我知道它正走向哪里,将告别什么,最需要跨越的难关是什么,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中国不只是向世界开放,还在向中国开放。
至于脚力,一是要站得住,也就是说写作者必须能够持守自己的独立精神。我所理解之独立精神,不仅要独立于权力和资本,还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一个诚心诚意的写作者,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不当的惩罚而在文字上复仇,也不因为得到什么好处而在文字上报恩。此外,更要独立于民众。尤其最后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尤其难。
我一直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奥里维为榜样。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像奥里维一样,不憎恨,不盲从,不高高在上,在一切狂热当中,能够保持目光明亮,能够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奥里维就是这样,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独立。其实,罗曼·罗兰乃至茨威格当年何尝不是因为这种独立精神而被群众围攻,被朋友孤立。人群何其势利多变!你指出皇帝没穿衣服需要勇气,指出民众没穿衣服同样需要勇气。庆幸的是,即使是被误解,他们还是在坚持。正如茨威格所说,世界上还有一种单枪匹马的英雄主义,一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在这种英雄主义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座城池、一个国家。
二是要走得远。前不久,有社会学专业学生撰文批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不得“方法”,实在是因为该批评者未能全面理解何为方法。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常常过于依赖表格——问题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消化这些数据。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充斥着各种图表,最后的结果是图像代替了文字,观看代替了阅读。更别说有些数据本来就靠不住。正如我在书中所引述董时进先生的观点:“……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唯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回想托克维尔当年写《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没有一张表格,甚至也没有堆砌太多的数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思考与写作的深度。因为他在旅行与观察中抽丝剥茧,已经消化了这一切。
我这样说并非认同写作者可以闭门造车。事实上,我一直坚持一个合格的社会学者必须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几年间,为了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查找了大量民国以来湮没无闻的旧书籍,包括董时进出版的所有著作,更别说与本乡本土历史相关的档案、材料和口述历史。此外,我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又岂是一般调查者所能获得。重要的是,我知道前面这些材料的意义并不只在于佐证我过去的观点,更在于发现新的问题。如果你过去的观点因为新材料的获得而动摇,那不是你的灾难,而是你的福气。
行走与思考一样,没有止境,或许我本可以让那些批评我的读者满意。《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后,我赶巧有机会去日本,浮光掠影地感受了那里的都市与乡村。我很遗憾未能早些到这个“绕不开的邻国”走一走,及时将我新的思考补写进我的这本书里。然而书就是这样,因为总还是要出版,总还是会有一个截稿的时间。而且,只要你一直在行走,在观察,在思考,就永远无法让自己满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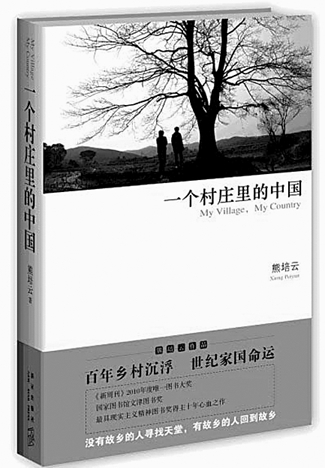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