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及作家和他们写作背景的关系,俄罗斯作家、俄罗斯文学和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最为相似。林贤治说,俄罗斯文学伟大与辉煌,在于以社会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而始终抱持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我们回顾俄罗斯文学的不同时期,那些作家笔下对民族和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通常会流露出无限的赤子之情。其实这两种创作情绪也往往出现在刚刚步入现代史的那一批中国作家笔下。中国作家在写作时面对的现实困境,恰恰是现实本身。从二十世纪初到今天,从时代主题上说是沧海桑田,而从微观来说,现实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人生的内容其实并无不同。今天,一个人被称为作家,是指他以写作小说为生,并且作品获得不同程度的认可。以此定义“中国作家”,他们生活在这一如既往的现实之中,而且他们是“敏感的一群”,不可能放弃对现实的思考。对现实思考的结果,决定了他们在写作中走哪条路。
我相信阎连科的写作曾经长久被遮蔽在街头文化快餐类杂志的版面上,反复被节选。一个中国作家,如果能有免于这样“被节选”的自由,那么接下来谈他的创作历程才有意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不单单袒露了自己的创作源泉,更使人发现他的写作在文本和现实面前长久的焦虑。这本对谈录《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现在看来是集中了阎连科对自己的创作母题,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长期思考的记录。
对现实的思考,对表现现实的思考,必然决定于事先对现实的深刻认识。阎连科讲他家乡的那个镇子,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他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他说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但合理的:二十八年前,阎当兵时村里是六千口人,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村里仍然是六千口人。三十年时间,村里兴旺发达,人们不生不死。村里已经二十年没有一对新人结婚,没有一对年轻人去领结婚证。道理非常简单,新人不领结婚证,就没有计划生育的问题。老人永远不死,就没有调整和上交土地问题。阎连科就此说,中国的社会别人无法想象,表面混乱,而内在里自有其秩序。这样一个莫名的镇子,正是中国千万村庄的影子,人们古老的生活,百年来的人生智慧往往用来抵御外界对他们堂而皇之的剥夺。“荒诞”所具备的冲击力,往往要胜过刻意营造的情节设计,就是阎连科所说的,“生活中美的东西少到几乎不在,而荒诞的东西多到无处不在,它不是走进你眼睛里来,而是一下子、一下子打进你的眼睛里来,打进你的心灵里去。”冷酷的荒诞,荒诞比现实更真实,是阎连科创作《坚硬如水》以来一直到今天所特有的写作视角。
《受活》出版后,有读者不满意,认为“受活庄”里面诸如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这样的故事过于“不真实”;后来的《丁庄梦》出来,大家同样不满意,因为它又太“真实”了,真实感太强了。人们既不满意《受活》中那种“不真实”,又接受不了《丁庄梦》的“真实”。这个例子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阎连科写作和思考的困惑,他说,这是我个人的困惑,也是文学发展到今天“现实主义的困惑”。在不停地尝试和体悟世界之后,作家渐渐从困守真实世界,而迷惑于荒诞的真实,向远方走去,走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束缚。于此同时,阎连科似乎也很介意将他的一些作品贴上“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牌,对于目前文学评论界惯用的“按照外国作家风格归类”和“与传统经典相扯相牵”都提出了批评。在今天西方小说创作论满坑满谷、“主义、流派”泛滥的时代,还有中国作家提出“当代文学除了传统和西方的影响外,它独有的个性、价值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不能不使读者见了觉得格外奢侈。
就这本书的价值内涵来说,最可贵地揭示了一种当代小说创作的有趣现象。即当代一些重要的小说作品,如《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丰乳肥臀》、《檀香刑》、《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马桥词典》、《万物花开》、《花腔》、《九月寓言》、《古船》等等,所写的故事都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都不是当下的现实。你会发现,这些作品的作者,那些成名的作家,对今天的现实似乎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迂回”。从忠实于内心写作的角度出发,这么做看起来有些逃避的意味。阎连科谈到自己的《日光流年》——也是一部可以归类在上面所举例子之内的作品,他说,就创作来看,故事要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保持一段距离,会更利于自己的写作,写起来会更畅快,更利于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脱离现实、对现实视而不见的理由。但是对于现实究竟应该如何表达,其实他非常迷茫。或许,对小说背景相同的选择,反映出的是一种集体的迷茫。因为你赶上了这现实,是这现实的一部分。你无法全身抽离出来,以完全清醒的“他者”的视野来书写;另一方面来说,今天思想成熟的作家,已经不再抱有“作家作为社会英雄”的想法,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写作。作家集体疏远于当代现实,不能说写不出经典,但总的来说并非时代的福祉。
阎连科儿时曾经有位语文老师,那时业余在家里写小说,据说写得比《红楼梦》还要长,还要好。当时阎已经读过《红楼梦》,于是对老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尊敬。这老师也特别高傲,每天上课的时候,卷一根炮筒子烟叼在嘴上,课又的确讲得很好。对阎连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位老师对人的那种傲慢。这种傲慢,他认为正显示了那个时代文学的高傲和神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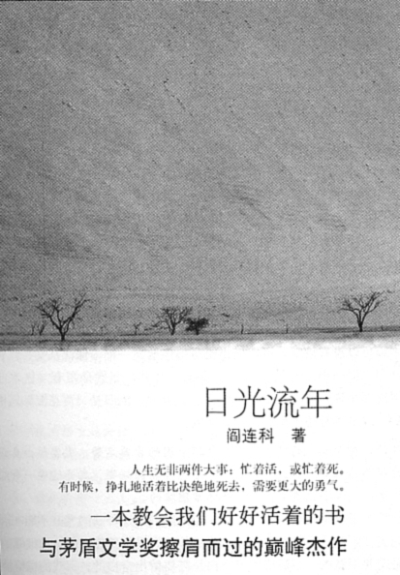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