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出来,我站在首都剧场的台阶上,竟生出“今夕何夕”的恍惚来。回想起刚才看演出时,时不时有种“一脚踏空、栽个跟头”的感觉。这个“一脚踏空”,是道理上不通畅,逻辑上的卡壳。
话剧讲的是蔡文姬流落南匈奴12年,曹操派使者去接她归汉,撰写《后汉书》,并默写其父亲蔡邕散佚在战火中的著作。蔡文姬想回国有所作为,又舍不得一儿一女,三日不能拿定主意。汉使周近误以为是蔡文姬的丈夫左贤王从中作梗,虚言威胁再不放人,曹操有十万大军在后,要荡平匈奴。因此激发了矛盾,蔡文姬一度认为曹操师出无名,任意用兵,自己宁愿老死匈奴。所幸另一名使者董祀大肆渲染曹操的文治武功、雄才伟略,不仅坚定了蔡文姬归汉之心,也打消了左贤王的疑虑。
歌功颂德从第一幕就开始了,董祀说丞相“爱兵如子、视民如伤”,“丞相用兵作战是为了平定中原,消弭外患”,“善用兵,但决不轻易用兵”,“期待的是四海一家”,所以是“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郭沫若曾直言:“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句话被印在节目单的最上头。1950年代末期,带着政治背景的为历史人物翻案之风,轰轰烈烈。而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这些远程的褒义词虽然有点啰嗦和重复,倒也不难接受。
真正的不对味和“一脚踏空”,是从第三幕开始的。归汉途中,蔡文姬因为一直思念儿女,夜不能寐,弦歌不辍,以寄悲哀。董祀来劝解她,开始说:“你要是(悲伤过度)昏倒了,我们对不住曹丞相,也对不起伯喈先生。”当然这只是一句常规劝人的话,不必过度诠释。可真要细琢磨起来,却多少有点别扭,首先是出现了“我们”一词,说明董祀表达的不是个人观点,而且好像他对于蔡文姬本人并无关爱,对其别子之痛也无体谅,他的善意开解只是为了不辜负曹操和死去的蔡邕,蔡文姬本人并非他的目的。
接着董祀说:“我们希望你把心胸放得更开阔些……请你多想些更快乐的事吧。”他所谓快乐的事,就是十二年后,在曹丞相的治理下,“百姓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边界安宁,这难道是小事?”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从大处着想,而沉溺于儿女私情里面?大姐,请你把天下的悲哀看成你的悲哀,天下的快乐看成你的快乐,那不就可以把个人感情冲淡一些吗?”
当蔡文姬继续强调自己个人的悲哀太深,总是扭转不过来时,董祀开始用一种责备和批评的态度说:大姐,你让我失望了。“到底是个人事大,还是天下事大?以前很多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你不曾这么悲伤过,现在怀念一对平安无事的儿女,却如此悲哀,你的心胸怎么这么狭窄呢?”
这一席话在剧本设计中很有力、也很有用,蔡文姬马上就豁然开朗了,振奋地说:“我要感谢你呀。你说得好啊,是起死回生的良药。”并用诗意的夸张发誓说以后要管住自己,尽量减少个人的悲哀,并兼程赶路,好早日见到曹丞相。
因为说得好听,又有奇效,这段话的大意在后面还多次重复。蔡文姬向曹操复述:“他责备我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他教我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像我这样沉溺在儿女私情里面,毁灭自己,实在辜负了曹丞相对我的期待。”丫头侍琴侍书也证实:“董都尉说,如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已和十二年前完全改变面貌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他怪文姬夫人为什么不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最后文姬总结说:“自从董都尉劝告了我,我的心胸开朗了。我曾经向他发誓: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我觉也能睡,饭也能吃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
这段台词在演出过程中引起了普遍的骚动和笑场,“新人”这样的词带着强烈的1950年代气息,从汉末的高级知识女性的嘴里吐出来,落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观众的耳朵里,有着惊人的时空扭转畸变的诡异效果。
董祀的那番话,并不完全是善意的劝解,而是意义确切的批评和指责。蔡文姬的自我检讨“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真是万分有罪”,也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在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我姑且承认这种“官方正面说法”),蔡文姬有否有权为自己的私人离别而悲伤?
古代交通不便,匈奴和大汉又分属有前嫌和龃龉的两国,蔡文姬和幼儿弱女的分别,不啻为生离死别,今生能否再见都不得而知,做母亲的因此伤心难过,该是基本的人性和情理,这跟国家是否昌盛全无关系。忧国和思儿是两种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情绪和情感,不能混为一谈,也没有什么可比性,更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在两者之间做高低取舍,或做是非判断,是一种越界行为。
这种界限的设定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国家意识和组织结构并非无所不能,有些事是它们管不了的。美国的政治科学教授格伦廷德在其《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里提到,政治哲学必须思考权力,而这种思考最容易在两方面迷失方向,或者误解生命的目的(权力应该用来干什么),或者误解权力的能力(权力能够干什么)。确实,国家和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它解决人的全部问题。国家再强盛,政治再清明,也不能让春天永驻,让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让人不生病,也不能消解一个母亲的别子之痛。而悲春感秋、失恋和所爱非人,为亲人的病情揪心,牵挂儿女,正是私人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重要的情绪源。
所以,国家和政府就必须对自己的活动范围有所限制,要知道自己的边界所在,将私人的问题交给私人。这种限制不是出于人间道义,而是出于天然法则。
可是,能力有限的国家和政府,却因为拥有公共权力,便必然地有了自然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如果不加以制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国家和集体相对于个人本来就有压倒性优势,个人情感和私生活一旦被所谓的国家利益绑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轻易地被贬低、漠视和践踏,“个人趣味”就是“低级趣味”,对个人的考虑则几乎可以直接等同于自私。通过这样的道德审判,引诱或威逼人“主动上交”私人领域的权利,主动消解自己的私生活,从而实现泛政治化的“存国理,灭人欲”。
学者们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讨论多了,孙隆基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时,也论到过中国人没有私生活,老百姓普遍“儿童化”问题。而我们的文化还一直过多地强调个人对于集体、国家的义务,而较少关注到私人的情感、生活应该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和尊重。
私生活之所以重要而且神圣不可侵犯,在于一个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或者国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性之于国民的义务,具有优先性和更本质的价值。就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言,国家只是手段,个人才是目的,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的存在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幸福,而个人并不是为了君王万岁或国家强盛而存在的。个人关心国家的唯一理由,在于国家能保障他的利益和权利,而且这种保障是他独自一人无法做到的。
既然如此,我们便该讨论两个问题:不能以国家的名义对私人做什么和要求什么?私人可以无条件地享有什么?
我想,蔡文姬有“心胸狭隘”、不大公无私的权力,在国泰民安之际,她仍然有权为儿女小私情悲伤,不应该因此受到责备和非难。而且,进一步说,如果蔡文姬为了儿女,终于决定不回汉,从而导致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永远失传,那也是她的个人选择和自由,应该被尊重。他人对此可以遗憾,却无权做任何道德批评。相反,一个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正视一个普通母亲的普通情感,不能尊重之,体谅之,同情之,那么,这一定不是个好的政府。
郭沫若自称:“蔡文姬就是我。”而整部戏就是在说:我离国多年,现在回来了,一开始思想觉悟还不高,对新政权新领导人有疑虑,而且太沉溺于个人的悲欢情怀,没有以国家天下为重。不过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折服于领导人的伟略和雄心,愿意跟着领导做新人,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去。这个尽忠效力的表态真是又高调又漂亮,郭沫若确乎是有才情的人。可惜剧本于1959年上演,复排演出则在1978年,期间的历史,尽人皆知,不说也罢。在国家政权膨胀并挤压私人空间和权限的过程中,《蔡文姬》一剧有推波助澜之功,而最终,无论郭沫若还是他的剧本,又是这波澜的受害者。更吊诡的是,这种推波助澜,形式上是帮助国家满足扩张欲,最后却不仅导致私人权利土崩瓦解,而且让国家政权本身也受到严重伤害,却也是历史的荒诞和反讽。
《蔡文姬》的最后一幕《重睹芳华》的原稿是《贺圣朝》:“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扫荡兼并呵诛锄豪强。乌丸内附呵匈奴隶王,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渡越周秦呵遐迈夏商。哲人如天呵凤翱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后来在排练中,导演和演员有不同意见,由田汉将歌颂的主题由曹操仍然改为蔡文姬:“巍巍周公呵吐哺握发,明珠赎我呵重睹芳华。”郭沫若最后定稿,又加了一句“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收束提升。
话剧终于在华丽的歌舞和齐声高昂的“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中结束了,其中诸多时代的隔阂和别扭,我必须加上“1959年”和“郭沫若”这样的信息补充,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格特征,一切才能被理解。但同样在这个剧场里,我看《雷雨》、《茶馆》,就不需要将自己格外还原到半个世纪前的情境中,也能无碍无遮地理解剧情。有此对比,我不禁想:文艺工作者固然活在当世,他们的作品却另有一个生命,孰长孰短?孰轻孰重?两者不可得兼时,创作者的心里该想着哪一头?
而另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多数观众都已经爆笑的今天,《蔡文姬》还在上演?我宁愿相信,那只是因为怀旧,因为广为人知的剧本荒,才会一次一次地重排老剧目。我确乎听到了来自观众席的叹息和哂笑,而不是感动或感染,这正是觉醒和进步。演出中“以天下为重”的宣誓言犹在耳,可天下本不重,因负载私人福祉而重。但愿《蔡文姬》激昂的时代真的已经渐行渐远,我们正一步步走向一个民众能够被真正尊重的光辉岁月。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编辑 宋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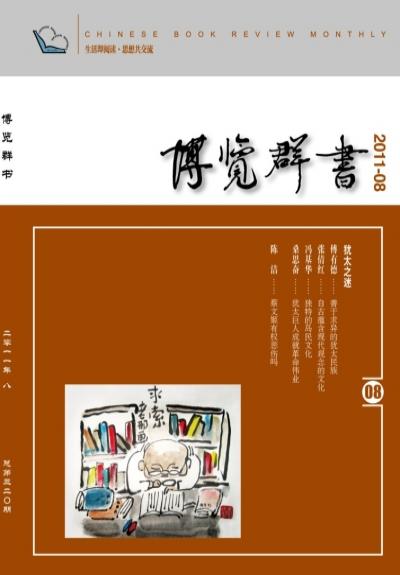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