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普通的外交官、建筑师兼诗人、独立制片人兼导演。他们是活跃在中国和以色列这东亚和西亚两端上的许许多多人之一。无论是CCTV还是CNN,网络媒体或是传统纸媒,有关以色列或是巴以问题的报道总是出现在显要位置。两年前我参与翻译了第一本描述当今以色列人生活状态的纪实文学作品——《以色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唐娜·罗森塔尔作为一名记者,采访了特殊国度上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以色列人,读起来让人久久回味。今天再次提笔写以色列人,情境有所不同,写的是我身边的以色列朋友。
自1992年正式建交算起,2012年中以将迎来建交20周年纪念,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两个同样具有5000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度,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不断尝试定义新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上是世界范围内的绝对小国,而中国相对而言却在大部分的领域,占据了全球范围内的总量前茅,这一大一小、源自不同文明的两个国家,却出乎意料地在对方的版图和日志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又一页。20周年和5000年文明间的对比和反差,有一丝扎眼,但我却认为,正是这样的一种不相称,促使我们不断抛开地理的阻隔、文化的差异,而走到一起。
有故事的前以色列外交官
以色列外交部中国事务主管、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副馆长、前以色列驻上海副总领事,这位有着一个浪漫中文名字——蓝天铭——的以色列朋友,最近正忙于安排来自中国的政府和商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的各项行程,在所有曾经踏上中国土地的以色列人中,他一定是最幸运者之一。刚过而立之年就已成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并被派驻上海总领事馆,又在这段任期内有幸担任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的副馆长,成为以色列首次以自建馆身份参展世博会的亲历者,回到以色列,又再次被委以重任,主管外交部中国事务。也正是如此,每当我们之间谈起他的下一次驻外工作,他总是会反复跟我强调依然会选择前往中国继续他的外交生涯,“固执”得有些可爱。
当蓝天铭5年前初任以色列驻上海副总领事时,因工作原因,我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单独会面。在坐落于虹桥开发区一座写字楼内的领馆会议室里,我们面对面打量着对方,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名副总领事,笑起来总是大大地裂开一张嘴,没有印象中外交官所具有的职业微笑,而我那时也才刚进入大学工作,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除了谈工作,自然还聊起各自的生活。从那个时刻,缘分就这么展开了。我们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进而又发现两人还是北大的校友,并且学的都是对方国家的语言,关系又拉近了一些。
此后的三年,我们俩成了搭档,无论我俩谁受邀做关于以色列的讲座,都会叫上对方一起,一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语言上形成互补,二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介绍各自眼中的中以两国。我们这个中以组合活跃了三年。有一天他交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他的婚礼请柬,再一看婚礼地点以色列地中海边一个叫Canaan Land的小村庄——这个婚礼地点似乎有些遥远。
如果说在出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开着车一路摸索着去Canaan Land的路上,还有一丝长途跋涉的疲惫与懊恼的话,那么当我站定在婚礼现场,身处这片充满以色列和犹太特色的小花园之中,所有那些关于犹太婚礼的疑惑与好奇一下子涌上心头。这既是挚友一生中独一无二的婚礼,又是了解和深入当地文化的最好课堂。在拉比的指引和上帝的见证之下,新人、家属和来宾共同完成了婚礼中传统的宗教部分。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拉比主持下的犹太教婚礼,最后新郎用力踩碎一只玻璃酒杯,告诫人们在幸福的生活里也不能忘记苦难的历史。
有故事的世博会以色列馆总设计师
那一年是2009,彼时,世博会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在婚礼现场,一位充满艺术家气质的以色列朋友坐在了我的左边,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1919年我的妈妈出生在上海”。这个和中国上海有着奇特联系的中年人,戴着徐志摩年代的粗黑圆框眼镜,穿一件和中山装有些神似的黑色双排扣西装,说话间总是能抓住你的心,我和他约定了第二天一大早去他的办公室看看。回到了酒店我才想起连他是做什么的都没有问。到了约定时间和地点,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车轮上沾满了厚重的泥巴,上了车,几个弯一转,停在了一栋写字楼下面,进到了顶层他的办公室,终于看清了门上的字,Haim Dotan Architecture & Urban Design LTD,原来此人正是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的总设计师——渡堂海先生。难怪婚礼上,两个唯一和上海扯得上一点关系的人,会被安排坐在一起。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谈到了世博对各自生活的影响,他因为世博而不得不暂时长期离开妻子和女儿,但他仍然把每天看到、听到和想到的通过诗歌和相机记录下来,发给远在以色列的亲人和朋友。他给我看那些文字和照片,给我讲那些瞬间背后的故事,讲他祖母带领着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白俄逃亡上海并借住在虹口区的往事,由此便有了那句“1919年我的妈妈出生在上海”。一幕幕镜头像电影胶片一样呈现在我眼前。于是,一个念头在我脑中开始构思,我们应该把如此美丽的故事谱写成一本书,一份爱,连同所有的辛酸苦辣分享给更多的人们。就这样,往后的一年里,他钻在工地里建造了后来被评为“十大最有魅力国家馆之一”的以色列馆,我在另一片文字和图片的海洋里搭建这本讲述中以两国跨时代、跨地域、跨语言的作品。
我在一份以色列参与世博会的考察分析报告里作了这样的比较,在统计20个热门国家馆建筑面积、总投资、参观人数和排队入馆等候时间的综合数据中,以色列以4100万谢克尔(约1200万美元)的最少投资、1200平米的最小参展面积,列“最热门国家馆”的第11位。这一方面得益于以色列政府的重视。在上海世博会筹办阶段,以色列是最早确定参展、造自建馆的国家之一;此外,场馆的设计理念和造型十分切合当今国际潮流。以色列国家馆设计师渡堂海倡导“建筑元素取自大自然”的设计理念,以色列馆“海贝壳”的造型蕴涵了“传统与现代交融”、“和平对话”、“回归大自然”等当前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其三,以色列国家馆确立的主题成功。以色列馆的主题“创新让生活更美好”,既与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相互映衬的效果,“创新”又提炼了以色列国家的最重要特色,同时,其“创新”的主题又表达了崛起的中国的内在追求。
世博会期间,各国展示了其各具特色的建筑艺术作品以及高科技成果,以色列也不例外。农业高科技、海水淡化、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早已被我们所熟悉,但个人认为那些由人来表现的内容却显得更有张力,也更有助于文化的诠释与交流。在担任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文化顾问期间,除去那些早已印刷在节目单上的活动,我喜欢独自一人游走在馆外的开放空间。我们尝试对来访观众做过问卷调查,也尝试过赠送以色列特色的纪念品,但更多时候,来自观众真实的声音,需要你以专业的角度但把自己置身于普通参观者中才能够聆听。
有故事的纪录片导演
就在那一天,我突然被馆外一个时而举着手机摄像,时而又把摄像头转向自己并且口中念念有词的观众所吸引,凭我的判断,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我也得知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绝非只是参观世博。
上海国际电视节在世博期间举行,纪录片单元有三部以色列影片参赛和参展,我辗转三日三个影院,一个不落把三部影片看完。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一部以第一人称视角,实战记录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某连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执行任务的纪录片——《Alpha Diaries》,片中出现的所有场景都是制片人、导演兼摄像师Yaniv Berman——那个我在世博园里“一眼相中”的以色列人——在5年时间里,一手扛着枪,一手提着摄影机在实战中拍摄而成。他不是战地记者,他甚至都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每年前往军队服1个月的预备役。但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影视专业的他,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外人所无法见到的珍贵画面,努力尝试还原一个真实的以色列,呈现给身处战争与恐怖袭击之外的我们。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某个巷战场景,战友们对他的照顾,掩护这个因为专注于摄影而经常不顾安全把枪搁置在一边的兄弟,当然还有闲暇时他们对摄影机背后那个人的“挖苦”与“讽刺”。军营生活枯燥但也历练人,你会发现每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身上都充满了某种悲壮但又喜剧的色彩,他们有些是天生的演员,在纪录片中的表现让人会误以为是专业演员按照剧本在执行导演的安排。甚至连炊事班的厨子都能给你来上一段即兴的炒菜歌舞曲。
Yaniv和我坐在小饭馆里,吃着点心,喝着啤酒聊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我们没有谈到有关影片的任何细节。而他却在回到以色列后不久把那些手机镜头中的上海,连同我们在饭桌上说的那些夹杂着希伯来语、英语和汉语的画面一起,编辑成了他上海之行的10分钟纪录片,上传到他的个人空间里,引来众多关注他纪录片观众的议论。
除了他的《Alpha Diaries》是来到2010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三部以色列纪录片中的唯一一部参展影片外,其他两部均入围参赛单元,并且一举拿下各自单元中的两个金奖(注:上海国际电视节共设三个纪录片单元,每单元设一个最高奖金奖)。以色列纪录片震惊了上海,而我却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以色列从来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世博会落幕后,除了极少数的国家馆得以保留,以色列馆也和其他大部分的场馆一样,需在原址拆除。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记得渡堂海布满血色的眼睛,似乎含着泪水地对我说,他无法站在那片工地上看着亲手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以色列馆就这么再次回到一片平地,他选择了暂时的离开,像一个中国文人一样,去浙江安吉听竹林涛声,去张家界把自己置身于山峦环抱中,去虹口区的老街道里继续他母亲生前托付给他的“寻根之旅”——“1919年我的妈妈出生在上海”。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希伯来语专业教师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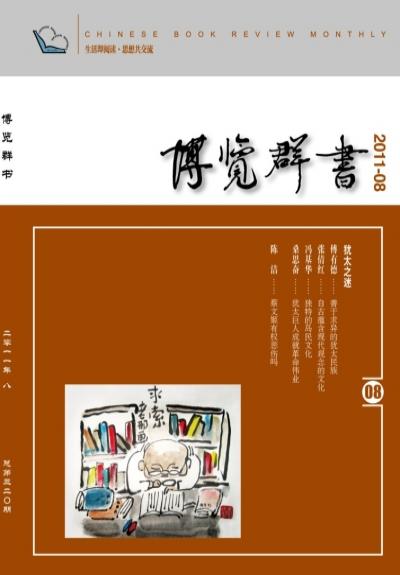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