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在世界语境里已经成为一个特定词汇,它往往特指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灭绝暴行。“大屠杀”给予人类的颤栗是如此深重,它以累累堆叠的尸骨、焚尸炉中深厚的人油、以及种种不忍卒睹的惨状确证了人性恶所能达到的维度,让“人”这个种群对于自身的人性产生了普遍的绝望。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二战之后对于纳粹的清算绵绵无尽且反复深入,直到今天,“反犹主义”依然是西方判断政治正确的一项标杆。刚刚过去的2011年戛纳电影节上,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在新作发布会上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来是纳粹,因为我的家人是德国人,这令我很高兴。”此言一出,一旁的女主角克尔斯滕·邓斯特不由得惊叫一声“天啊”,拉斯·冯·提尔接着说:“我理解希特勒,他肯定做了些错事,但我想我了解他,而且有点同情他,但我不是赞成二战或者反对犹太人……我当然支持犹太人了,但以色列真的很讨厌,我应该怎么说呢,好吧,我是纳粹。”
即使拉斯当时的语气带着开玩笑搞气氛的意味,但他得到的结果仍是第二天就被戛纳官方宣布为电影节“不受欢迎的人”,就算他发表了道歉声明也无济于事。这证明“反犹”在西方是绝对不能碰触的话题,即便因此与“言论自由”的原则相抵触。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遭到了敌视?为什么这种敌视会上升至仇恨,并在过去的年代里具备如此普遍的“群众基础”?犹太人的民族性竟至于被嫌恶至此吗?
命运多舛的犹太民族
毫无疑问,犹太人之命途多舛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脱胎于犹太教,然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纠结与争战却从无尽时。基督教曾受到严酷迫害,犹太教亦复如是。三个宗教之间的恩怨缠斗,映照出各种人性纠结,那是信仰的“巴别塔”。
对于犹太人的敌意,从基督教执掌势力的漫长年代就已被反复确立。在罗马帝国治下,犹太人每七天休息一次的习惯都成为民众的笑柄。彼时,官方立法虽认可犹太教,然而在整个帝国的种族中,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不得不每年向“犹太财政局”进贡的民族;皈依犹太教,或者为生下来不属于犹太教的人行割礼乃是死罪;犹太人也绝不可能被提升到古罗马元老院成员的尊贵地位,就连犹太人自己也并不指望能到政府中任职,或当议员和骑士。在康斯坦丁大帝的统治下,犹太人被称为是“渎圣的一群,恶毒的一派”,禁止基督徒与犹太人通婚;皇帝西奥多二世在位期间,作为“宗教法庭的第一个基督徒审判官”,他极其严酷地把犹太人赶出了所有的公共机构;西塞巴国王登基后,连犹太人的孩子都被掳走,送到正统天主教家庭中抚养成人。
对犹太人的屠戮,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十字军的一些领导人曾发誓说,基督的血要用犹太人的血来偿还。西塞尔·罗斯在《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中说:“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小股杂牌军和那些跟随在大部队前后的一群群武器简陋的狂热农民。当时,他们都普遍相信,只要杀死一个犹太人,所有的罪孽会得到宽恕,炼狱之苦也会得到赦免。”杀戮残暴到什么程度?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暴行的瘟疫已经传染到英国,在约克郡大城堡里避难的犹太人为了不让敌人享受屠杀的快乐,从拉比开始,所有家庭中的户主都杀死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再互相杀死。西塞尔·罗斯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暴行的头目都是曾同犹太人做过金融生意的小贵族阶层的成员,他们金钱上的负债即使没有引起,肯定也增强了他们的宗教狂热。”
世俗对犹太民族难以理解的敌意
与其追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莫如追问“为什么人性会如此?”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以及他们将“殉教”作为一种荣耀而引发了非犹太教徒普遍的敌意,为什么宗教狂热会带来如此的残暴?为什么残忍会具有如此的传染性?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中曾经写道:“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钱……在他们的眼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而且他们确认,在这块大地上,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
这番话堪称尖刻,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反犹,而是借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他在文末说:“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虽然马克思整篇文章都在批判金钱的异己本质,他毕竟使用了“犹太人狭隘性”来对资本和金钱做一个形象的指称。追逐金钱或许不算是一个美德,但至少不能算是一项罪恶吧?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的问题》写于1843年,乃是为了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对犹太人的言论而作的。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道:“例如在维也纳只不过是被人宽容的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力的犹太人,决定着欧洲的命运。”马克思对此段文字评论道:“这并不是个别的事实。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
富有、会做生意,是大多数人对于犹太民族的共有印象,奇怪的是这一特征也能招致普遍性的不安。一个没有国家和国土、流散在世界各地、千百年来始终处于政治地位低下的“卑贱”人群,通过金钱来获得生存的安全感,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
从17世纪后期起,在国家威望和经济与商业利益的新扩张两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要,而欧洲居民中没有一个群体打算增加国家的威望或积极参与国家商业的发展。因此很自然地,犹太人由于世世代代充作放债人的经验,以及他们同欧洲贵族阶级的联系——时常寻求贵族阶级的地方庇护,并为贵妇阶级处理金融事务——而会应邀帮助发展商业。很明显,正是出于新的国家商业的利益需要,才允许犹太人享有某些特权。
犹太人做生意的传统由来已久,在9世纪的法律文件中,“犹太人”和“商人”两个词有时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汉娜·阿伦特所言“世世代代充作放债人的经验”,起源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及之后,对犹太人的歧视甚至于将他们驱逐出了商业组织。但就在这时,一种经济上必不可少的职能出现了,中世纪社会对此毫无准备,那就是金融家,或银行家,或放高利贷者。王室需要资金来开拓疆土进行征战,贵族需要贷款来从事新的投资项目,普通人需要购买各种原料……这使得犹太人得以和政府达成亲密关系,成为王室的金融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并未改变千年来人们对于犹太人的成见。听听布鲁诺·鲍威尔的口气,他是如此回应德国犹太人对于解放的渴望的:
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你们犹太人,要是为自己即为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你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奋斗。而你们所受的特种压迫和耻辱,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例外;相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证实。
言下之意就是:“既然犹太人不关心德国人的解放,为什么德国人该关心犹太人的解放呢?”
汉娜·阿伦特——一个王室金融顾问,并且并非因此获得永久的特权与庇护的犹太人——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扩张随着暴力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使国家具备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地位。这意味着犹太人慢慢地、但是自动地失去了他们排他性的独特地位。国民们意识到,他们的个人命运越来越紧系于国家命运,这使他们随时准备向政府提供更多的信贷。
不问政治只重金钱
汉娜·阿伦特是二战以后西方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是犹太人,她认可自己的犹太性,却不愿意信奉犹太教,也许因此才让她从历史根源、民族心理等各方面如此深入地对犹太民族进行解剖。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指出犹太人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关心政治只专注商业的习惯,这导致“犹太银行家的效忠对象迅速地从一个政府转变到另一个政府,即使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后亦是如此。184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在不到24小时里,就从路易·菲利普政府转向为新的、短命的法兰西共和国服务,后来又转向拿破仑三世”。这种政治上的无知,难免让犹太人在民众中造成了“有奶便是娘”的恶劣印象。汉娜·阿伦特说:“犹太人从他们的历史经历中多少得出了结论,即当局,尤其是高层统治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低层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对他们是危险的。”
为何会如此?汉娜·阿伦特分析认为,因为犹太人风格是由特别的歧视和特别的受惠这两者构成的,“然而,歧视和吸引在政治方面都不会产生结果。它们既不会产生反犹政治运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保护犹太人不受敌人侵害。但是,它们毒化了社会环境,颠倒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关系”。
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79年,由极为偏激的威尔海姆·马尔定名。
祭起“爱国”大旗的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太容易走向极端,一旦走向极端,那些民族主义者几乎全然自认为本国优于他国,其中最极端者,甚至会寻求摧毁非我族类的文化。民族主义永远都是社会的一股潜在力量,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若轻易煽动民族情绪,几乎都会立即开启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很不幸,犹太人始终处在与之敌对的民族主义的围困之中。追根溯源,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是一个犹太人,这种世代遗传的情感仇视成了一种文化积淀,浸润于民族情绪之中。汉娜·阿伦特说:“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桩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
早在希特勒煽动起德国全境的反犹情绪之前,就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有一个犹太秘密国际组织,自古以来就有野心去统治世界。《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中指出,在20世纪初,一本所谓《犹太人圣哲议定书》“不间断地一版又一版用各种语言出版发行”,书中声称一个名为“犹太国际”的组织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协定,以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并且连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都已拟定。
相信这个传言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不光是希特勒,在希特勒死后六十年,200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仍在说“犹太人利用代理人统治世界”。这种说法称犹太人在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和阶层都已占据重要位置,图谋控制全世界。
如果从人性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说法或许折射了人们对于犹太人可能实施报复的恐惧——犹太人被歧视仇恨了几千年,难道他们就不仇视非犹太民族的人吗?难道犹太人不也具备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拒绝被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同化吗?难道犹太人一旦掌权就不会疯狂反扑吗?
“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人被人类的残暴吓住了,人被人性恶的基因惊呆了。二战之后,世界共识开始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寻求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观点,犀利地指出普通人群随波逐流附庸作恶也是应该清算的,同时也犀利地指出犹太人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违反了程序正义。
文明发展到今天,犹大的罪归犹大而不能归于犹太人,应该具有普遍的共识了吧?“诸众”概念正在逐渐替代“人民”的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诸众”代表了无法化约为一的复数性。“人民”是一张巨大的面目模糊的脸,而“诸众”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个体。
这当然是文明的进步,然而在举步维艰的进步当中,又有一个观点开始流行——犹太人将“大屠杀”变成了对己有利的武器,只要牢牢抓住这一道义上的优势不放,犹太人不仅能确保自己的种族生存,更能在西方统治的这个世界中通过控制西方的大脑从而实现犹太人隐形的世界统治。
时至今日,犹太问题依然无解,并被拖入了各种新的观点与势力的角斗当中。这不仅是犹太的困境,更是人性的迷途。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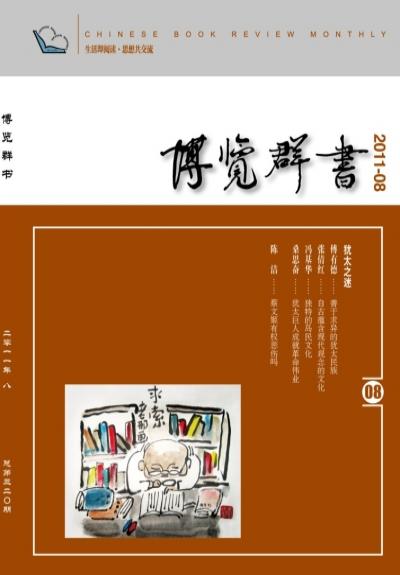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