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只是一个传说”这句话,我是在2010年央视春晚上第一次听冯巩说的。当时,众皆大笑我亦笑之,但并不明个中缘由。过后方知这是一句歌词,来自网络流行歌曲《不要再迷恋哥》。歌中唱到:
请不要再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但是我,还是要说……每一个传说都会随着时间褪色……
想不到,年轻人的歌吸引了不再年轻的我,让我想到了很多。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传说,仿佛一切都是传说。
或许,我们就是一个喜欢传说的民族。不信你看那“黄土高坡”,香火缭绕,华盖如云,轩辕黄帝祭祀大典“进行中”。其实那三皇五帝原本就是传说的时代,无从考证,并不像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殷商的甲骨文那样可“眼见为实”。
远古的“那些事儿”没法说,且说近代。早就听说,《天演论》的编译者严复与日本明治维新九元老之一、日本第一位内阁总理伊藤博文,是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而且伊藤视严复为高才生。然近来方知,此两人虽都留学英国,却未曾同学,因为伊藤较严复早去了好几十年。
严复虽然不能像伊藤博文那样出将入相,纵横捭阖,但他的《天演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死水微澜的近代中国,其影响之大可谓石破天惊。严复把进化论思想概括为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告诉国人,古老的中国若不变法图强,必将在遵循“丛林原则”的近代国家的残酷竞争中灭亡。但是,严复的《天演论》并非直接译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是根据赫胥黎的文集编译而成,且夹叙夹议。其实,赫胥黎在他的文集中强调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是不同的过程,而严复却直接依据生物进化阐发社会进步。南橘北枳,理论联系实际。没办法,国情紧急!
其实,我等“贫农的好后代”(也是一首歌)本不知《天演论》为何物,只因在那19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火如荼,毛主席曾与姚文元讨论此书,一时天下为之肃然。说实话,至今我也不明白这事件究竟是何意义,或许那善使“金棍子”的文痞太接近猴类,需要专门进化一下也未可知。
赫胥黎是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他文笔犀利,雄辩滔滔,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1860年,也就是《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他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围绕进化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赫胥黎从此名满天下。其时,进化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聚集一堂,鸦雀无声。大主教在力陈进化论的虚妄和荒谬之后,没有忘记关切地询问赫胥黎:既然你承认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那么你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是猿猴呢?赫胥黎立刻反唇相讥:我不会因作为猿猴的后代而感耻辱,却会因成为背叛知识、玷污科学和坚持谬误的人的后代而感耻辱!科学与宗教,真理与谬误,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激动人心的宣言,激动人心的时代!据说,有一位高贵而虔诚的女士当场就晕倒了。但据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文献记载,参加这次辩论会的每一人“都很愉快”,辩论的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会后大家还一起“和颜悦色地共进晚餐”。怎么会这样呢?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恩格斯语),支持者承认它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反对者的质疑有一定道理。
部分神学家之所以不接受《物种起源》的观点,不仅仅是出于宗教情怀,而且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应当来自对于经验事实的归纳。他们深刻地指出,达尔文始终不能让人们看到,可以显示同一地区的物种连续变化的化石记录链条。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时序的化石堆积。因此,进化论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对于这种质疑,事后达尔文耐心地回答说,要在同一个位置找到在时序上接近的化石岩层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基本上无法看到显示同一地区物种进化的完整的化石记录,而只能根据从各地收集来的化石按照时序建立纵向系列,寻找物种进化的连续而微小的证据。生性温和的达尔文甚至争辩道:“其实我也倾向于把自然选择看作一种假设,但既然这种假设可以解释几大类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来接受。”
事实上,达尔文的思想是伟大的,人们的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生物进化的历史十分漫长,人类的历史与之相比过于短暂,而人类研究生物进化的历史就只在转瞬之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为进化论提供充足的证据。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自然界所存在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生物就是物种变异的结果。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有一只“聪明过人”的热带蝴蝶,虽然它的寿命至多两周,却立志研究人的生命。毫无疑问,这只蝴蝶根本无法完整地看到人的生老病死的一生,那么,它可能采取的科研方法就是——根据它所见到的不同状态的人推测:人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科学追求真理,但真理是通过“猜想与反驳”逐步逼近的。
在《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进化论一直在进化。当年达尔文虽然相信物种的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遗传学一无所知,即使天才的达尔文也是如此。否则,达尔文可能就不会与自己的表姐(他的亲舅舅的女儿)结婚,此后不断因他的儿女或过早夭亡或病魔缠身而痛苦不堪了。当代科学确认,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原本一家。特别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破解了遗传信息如何传递的秘密之后,进化论的三大原理,即物种变异、自然选择、万物同源,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当然也被部分地修正。
对于人类思想史来说,达尔文进化论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目的论对于生物领域的垄断性解释。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有机界是某种具有更高目的的超自然的力量所专有的领域,因为有机体的行为常常表现出某种目的性和计划性。达尔文则告诉人们,有机体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是其生存本能的表现,是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结果。有机体不存在超自然的力量所赋予的目的,生命现象与物理过程一样可以通过因果规律来解释。一言以蔽之,自然有历史但无目的。
1882年和1883年,人类思想史上的两颗巨星——达尔文和马克思——相继陨落于英伦本岛。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他把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他说,就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说来简单,就是人们必须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可能去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也就是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一个时代的社会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观点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通过这一基础去解释。而在马克思之前,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往往颠倒着看问题。
恩格斯将达尔文进化论称之为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并认为它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他告诉我们,社会历史与自然界一样没有目的。虽然参与历史活动的人,或激情迸发或深谋远虑,处于不同的动机,各有自己的目的,但由于人们的意愿往往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由此使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表现出发展的盲目性与偶然性。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强调,表面看上去混乱无序的社会历史是受其内在规律支配的,这一内在规律隐藏在人们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活动之中。一言以蔽之,社会历史无目的但有规律。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恩格斯曾详细地描述道:他们“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工厂主“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极富社会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义愤填膺。恩格斯告诉他的工人朋友:“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我愿意……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工人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它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还设想,在暴力革命之后,应该有一个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但这只是一个临时中断民主与法治的应急状态。实际上,在马克思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极少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改善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完善,晚年的恩格斯连暴力革命也放弃了,他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通过议会选举的民主程序上台执政。这就是著名的“恩格斯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恐怕不会想到,“无产阶级专政”在20世纪的俄国被固定为一种国家制度。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人的教科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无一例外地按照下述“五阶段”依次过渡: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马克思还曾按照“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阶段”。
让我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虽然我们的那些一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息的先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但由于不懂历史规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没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比如,被钦定为“奴隶社会”的夏、商、周,实在没有成规模的奴隶劳动。不仅如此,周代竟然“裂土分疆”,实行分封制。再比如,被钦定为“封建社会”的秦汉直至明清,社会的主体制度是皇权至上的郡县制。各位皇帝要么“众建诸侯少其力”,要么直接“削藩”,必置残存的分封制于死地而后快。好不容易等到明清末年,可那“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怎么也不能“自发地”产生出来,万般无奈,只能等待英国人连同鸦片烟一起从境外往里走私了。
看来,从前的“那些事儿”真不好说,还是上网听歌吧:“请不要再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但是我,还是要说……每一个传说都会随着时间褪色……”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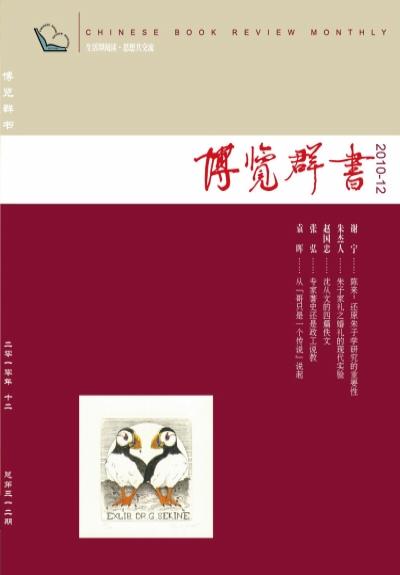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