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喜欢蹭旧书店,每到一地,必定逛逛,去不了的,去信邮购。原因简单,旧书便宜。所买的旧书上,有的有原主人的题记。这些题记,与学者考订版本源流、评骘内容得失、阐发著作内蕴等不同,只是用短简文字,或记下购买时间,或描绘读书环境、心情,或抒发一点感慨。当时未曾注意,待它们躲过“文革”浩劫,重读其中的几本时,觉得这些题记似显示了上世纪20-60年代读书人的文化底蕴和读书境界,或许可以把它们看作反映社会、人生的小小窗口。
上海文明书店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版线装书《宋元明文评注读本》(王文濡评注)。封面上钤有两个印章:一曰“熊超”(隶体,阳文),一曰“章轩”(篆字,阴文)。封套里有两首七律:
杜鹃何故尽情啼,我有忧思正惨凄。残梦已随春雨断,黛眉空羡远山齐。儿怜幼小情稍重,病恋家常语渐低。十载因缘今沦幻(原注:继室来家十三年),新坟独映夕阳西。
为遣悲怀竟二遭,问天不语首徙搔。有生辗转怜卿苦(原注:三岁丧母,寄养于四叔父母及幺叔父母),临死觑希我劳(按,“我”字前似漏“叹”字)。床笫难支柴骨瘦,闺讳(按,似应为“帏”)长静月轮高。灵子可是能来否?暂拟招魂学楚骚。
题诗之人肯定久已不在人世了。他受的是旧式教育,读私塾、学对课、写诗词。我读过一本与《评注读本》出版时代相同,由蔡元培先生审定的《全国学校国文成绩新文库》。这实际是全国中小学生的优秀作文选,内容多为诗词,尤以七律为最。可见,写诗是当时必须具备的素质。兹举《新文库》中一首与《评注读本》上所题之诗格调一致的七律为例。诗题《挽韩君》,诗曰:“英才济济苦沉沦,屈指年华十七春。天上玉楼频赴召,人间秋水总伤神。可怜此地销魂树,顿作他乡化鹤人。我亦凄凉频洒泪,茫茫世路一风尘。”当然,这位挽17岁亡故的韩姓同学的写诗人,无疑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而《评注读本》上的题诗人,则已是有过两度婚姻的成年人。他大约是读到《评注读本》中“哀祭”部分时,联想自己连丧二妻,于是悲从中来,发而为诗。两首诗,一悲己,一悼亡,真情毕露,令人同情。这本《评注读本》也许不只卖过一次,“熊超”“章轩”也不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管如何,实话实说的诗作,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和读书生涯的一个侧面。我读时,竟无端地萌生了一缕淡淡的物换星移、岁月沧桑的感喟。
上海贝叶山房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初版《唐诗纪事》(明·洪楩校本,标点者冯蕸卿,主编者施蛰存,发行者张静庐)。书主叫汪珠浦。第二册末有工整的毛笔楷书:“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十六日阅讫。时大雨霏霏,寒窗风吼,特识之。珠浦。”第四册末有同样字迹:“民国卅七年(1948)一月廿三日阅讫,汪珠浦识。时正大冻不介(‘介’疑应为‘解’)。”这位汪先生在寒天冷冻之时呵手读诗,遥想其境,令人忆起北宋陈与义的“客子光阴诗卷里”之句。
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文史通义》(章学诚著)。书主署名“朝阳”。书中有两处流利潇洒的钢笔字,一在扉页:“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进肝炎疗养院之第一日购于武昌街道口新华书店。”(按,街道口是武汉大学校门处)一在书尾:“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深夜粗读完毕,时风雨侵窗,蛙声欲裂,在疗养院宿舍。”一月之久,治病之余,将一本厚厚的文言学术著作读完,朝阳先生学力匪浅。题记简洁,颇含诗意。也许是平日忙于工作,只有进了病房才有完整的读书时间吧?这又使我想起了苏东坡的诗句:“有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提到诗,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散文集《春雨集》(陈淼著)的书末,有原主人题的名为《安陆轮》的“五绝”:坐上安陆轮,浑身都不行。买饭不及时,饿头昏眼花。(按,似可改为“眼花头又昏”。)我读后大笑,当即掏钱从书摊上买下。你想,饿得头昏眼花,还在读清丽的散文,心头春雨飘洒,牢骚自行消化。这真是一种难得的读书境界。
“文革”前最后买的一本旧书是从上海福州路邮购的。那是上海北新书店1931年7月第七版《野草》(鲁迅著),不切边,古朴、典雅、庄重。原书主人用毛笔在扉页的题记是:“1931.10.6暨香千购于开明书店。”(我由此始知有“暨”姓。)只点明购书的时间及地点。书的版权页上表明这第七版的印数是17001—20000本。我想象着:1931年“九·一八”之后18天,一个叫“暨香千”的读书人,是带着怎样愤懑的心情走进开明书店购买鲁迅先生这本著作的。书邮到之日,我在扉页上乱涂了一行:“此为《野草》初版之原貌,不意于1966年5月在上海旧书店邮购得之。66.5.14附识。”近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书到手之日,正是十年浩劫的前夜!这本书两次被购,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受难日相关。
(本文编辑 杜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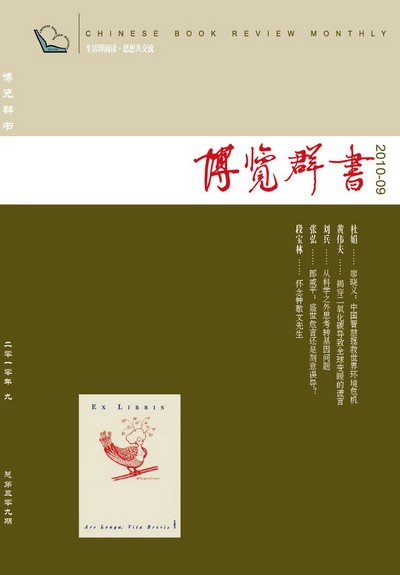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