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史专家梁吉生教授精心编撰的三卷本《张伯苓年谱长编》(下文简称《年谱》),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呈献给广大读者。展读是书,收获与感慨良多,亟愿向广大读者和所有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感兴趣、关注当今教育事业发展的同好们推荐。
一
年谱是一种记载和反映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传记类史书。“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李士涛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朱士嘉序》,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历史上,年谱之作始于宋而盛于清。近代以来,名人辈出,相应地名人年谱的编写与出版也倍受重视。一部好的年谱,其学术价值与作用,丝毫不亚于人物传记,而其本身内容、信息、资料和细节的丰富,更是远胜于传记作品,诚为研究历史人物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正因此,年谱的编写虽历来为学界所重,但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编写者不仅需要化极大的功夫,熟稔谱主的生平、思想及各种活动,对与谱主有关的各种资料做穷尽式的搜掘网罗;同时,还须具知人论世的慧眼和能力,在对谱主及其时代准确把握、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对各种资料做披沙拣金、芟汰冗杂、排比归纳、考订鉴别等工作,既系统、全面、真实、可信地反映谱主的一生和活动,亦寓编写者恰如其分的褒贬评价于其中。因此,编写一部好的年谱,所需功夫、气力和水平,绝不在传记之下。所以,许多有影响的大部头年谱,往往是多位学者分工合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如著名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和《毛泽东年谱》等。而以个人之力编写年谱,非有特殊因缘并经多年积累,甚或穷平生之力而不为功,如高平叔先生所编《蔡元培年谱长编》、来新夏教授编的《林则徐年谱》等是也。也正缘此,现世学人多视其为畏途,很少有人愿以此项投入多、费力甚、要求高,却“产出少”的工作为志业。故时下各类史著虽层出不穷,然由个人编写的好年谱却日见稀少。这也是面对《张伯苓年谱长编》而令人眼前一亮、肃然起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年谱》的作者梁吉生教授,多年来以其对母校南开大学历史及其缔造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诸多研究成果而享誉学界,由他独力编写的首部《张伯苓年谱长编》,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作者的深厚情感与全身心的投入。
作者自谓“编辑张伯苓先生传记资料的心愿由来已久”。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随着对张伯苓资料接触、了解的增多,“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意识使我萌动了一种想法,即编写张伯苓先生年谱”。(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自序》,上卷。本文凡未加注释的引文,皆出自该书自序)这种发自内心的冲动和历史责任感,随着作者此后对这位南开之父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愈久弥坚”,驱使和激励他在几十年间孜孜以求、不计得失,矢志于“追溯张伯苓颠簸踯躅、富有传奇的风雨人生,探析他那永不颓悲、执著无悔的生命历程,记录他那复杂坎坷的命运轨迹”;“把年谱编写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任务”。他长期投身于各种相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甚至已将之作为自己长期生活、抑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研究对象的品格、精神,也在无形中给研究者以极大的影响,使其工作本身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崇高和使命感。因此,他在搜集资料、撰写研究中所花费的心血、投入的精力,是难以计数的。诚如作者所言:“这些年来,我主要做了一件事,思考了一个人,积累了一堆故纸。这个人,就是张伯苓先生;这件事,就是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这堆故纸,就是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
这种源于情感、使命,在几十年间全力以赴从事的研究与写作、所下的功夫,不仅是“年谱”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与时下一些学人“只为稻粱谋”而快速、高产的“注水书”不啻有霄壤之别。
二是具有翔实、完备的资料基础。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以“用料真实、用功精到”(《张伯苓年谱长编·序一》P2)八字,给“年谱”以恰如其分的评价。翔实、完备的资料基础,的确是决定该书分量的关键,又是作者长期呕心沥血、广搜博采、日积月累的结果。作者自谓:“二十多年来,不问朝夕,奔走各地,访贤问友,或侧身故纸堆中,广事搜求,博采众言,精心考订,本着客观、公正、求真、求实的精神,不因人废言,亦不因对谱主事功的好恶,而弃片言只字,以期真实全面地接近张伯苓,为今人和后人的研究保存更多的历史信息。”(据张岂之:《张伯苓年谱长编·序二》P4)为此,作者不仅遍览南开存留的学校档案、出版物和天津当地的有关报刊、资料;而且利用一切机会,走遍国内的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山东、杭州、成都、重庆、自贡、昆明,甚至美国那些当年张伯苓足迹所到之处,“通过各种方法,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中查找资料线索”。他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即委托耶鲁大学友人代为查询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的档案,还在2006年亲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中心查找资料,以尽可能地“竭泽而渔”。“这样年复一年地努力,由简到繁,广事搜求,爬罗剔抉,钩沉稽疑,不问朝夕,不避寒暑,积以时日,谨敬收藏,居然有了近百万言。”这在该书下卷的附录七征引文献中也有具体的反映,其中仅征引书目就有220种,不少是难得一见的未刊稿和油印、手抄本;征引各类报刊39种,其中南开历史上的校报、校刊就有20余种;还查阅和征引国内外10家有关档案馆、单位收藏的档案资料。与此同时,他还不惜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拜访历届的南开校友做‘口述历史’”,用口碑资料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
在该书下卷的附录二至五中,还全文收录了1944年张伯苓写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喻传鉴写的《七十年来之校长张伯苓先生》,王斗瞻写于1947年的《张伯苓先生事略》,以及编者所收藏的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教授在1951年4月8日张伯苓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等一批重要文献,为读者和研究者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及当时人对谱主的评价。
梁吉生教授为编写“年谱”所做的资料搜集工作,尤其是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尽量搜求和掌握,颇似清初学者顾炎武对古昔学者治学如“采铜于山”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的褒奖。正是由于作者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积累,采集了如此多的资料“富矿”,再加上精心的熔冶,才有可能打造出“年谱”这样的学术精品。事实再一次证明,任何足以传世的学术著作都离不开这种坚实的基础性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是以深入的研究、史家的眼光统领年谱的写作。
“年谱”资料丰富,但绝非只是资料的堆积,而是取舍精当,编排有序。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始终有很高的学术自觉和极为严肃的科学态度——“用学术研究带动年谱资料的搜集”,以及整理、使用和年谱写作的全过程。早在动手编写该年谱之前,作者已发表了几十种专门研究南开校史及张伯苓的系列论文和著作,编写了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20集电视连续剧《张伯苓》,对研究对象已烂熟于胸且有许多独到的认识。而“年谱”可以说是作者用功最勤,耗费心血最多的集大成之作,是对其以往系列研究成果所作的一次整合与升华。
所以,该“年谱”的学术内涵已远非一般年谱类书籍所可比拟。它“无疑是认识张伯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基本上反映了张伯苓一生的业绩,展现了他从事教育实践、政治活动、文体和宗教事功的主要经历,追踪了他的人生过程;基本上提供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全宗档案,也可以说是张伯苓的履历史、生活史、思想史、精神史”。展读该书,益发深信作者的自信实非虚言。书中所记的每年、每月,甚至每日之事件,所用的每条资料,可以说都是经过作者的再三斟酌和精心安排,自然而然地以一言一行一事,不仅令人信服地勾画出张伯苓作为一位伟大教育家丰富多彩、曲折多面的完整历史和生动形象,而且很好地展现出其博大的精神世界和独特风范,使一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谈笑风生,豪爽豁达,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辩,倔强而克己”;“能从辛苦中得快乐,从失败中找成功”;“严肃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的教育家形象,深深地刻写在每一个认真读者的心头,使人久久难以释怀;从而不能不心悦诚服地认同作者的结论:张伯苓“从天津一个普通民居中走出来,抱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竟把一个最初只有几十个人的私立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的系列学府……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为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和民国时期“办教育的状元”(颜惠庆语)。教育是他“青年时的志愿,中年时的生命,老年时的安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可以说,“年谱”不仅是作者自身对张伯苓研究当之无愧的压轴之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新起点;同时也为今后编写年谱类书籍树立了又一个成功的典范。
近代以来,中国新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端和成长,离不开几代教育家的辛勤探索和杰出贡献。一百年来,每一所成功的学校,几乎都和这些教育家们的奉献和努力息息相关。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前夕所提出的:“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的讲话: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2009年10月11日)这也是时代的呼唤和迫切要求!因此,我们更要感谢《张伯苓年谱长编》的作者和出版者,该书为人们生动、具体地展示了一位前辈教育家成长的过程、事业、精神和贡献,使人们有可能更加真切地感受、认识什么才是以及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其意义、启示该是多么重要和及时啊!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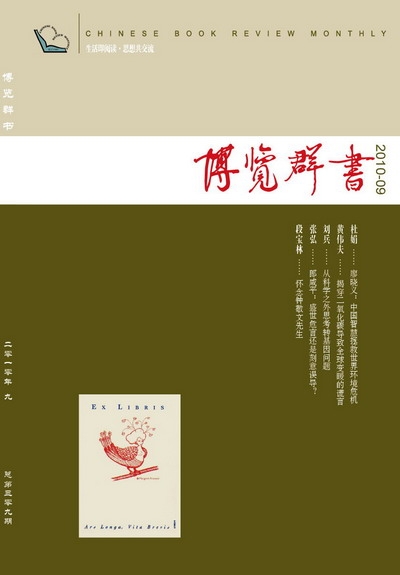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