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这个东西,会的人很多,画得好的极少,画得好上加好的,可以说是少而又少,邢先生当然算是少而又少的。
丰子恺大师与邢振龄先生的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别开了中国画的新天地。他们画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但又是以小见大,画的是活的人生,活的社会,所以他们画的是历史,是历史的画,是与历史永存的。
“晨起舞墨夜读书,错将花甲当花季。”这是邢振龄先生写的诗,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邢振龄先生很勤奋:去年初,他在宏宝堂举办了“邢振龄孺子牛画展”;十月份又举办了《邢振龄人间情味水墨小品展》。两个展览的数百幅作品,世态万象,构思各异,韵味生动。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出的作品不到一周,全部被购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是近年来北京琉璃厂未曾见到的景象。
邢先生的画有许多大人物都评论过,包括大诗人艾青、大作家汪曾祺等。艾青说:“读振龄的画,就像见到在阳光下沾着泥巴、蹒跚学步的农家娃,质朴,可爱。”艾青的话说得很是中肯,他告诉我们,邢先生的画离生活有多近,跟生活有多亲,阳光下的泥巴,农家娃的质朴、可爱,在邢先生的画笔下实在是生动极了。大作家汪曾祺评论邢先生:“是天生一双丹青手。”谁都知道汪曾祺是画中国画的高手,在字、画、文章等方面修养可谓深厚,通过他的评语我们知道了邢先生是大智慧的人,在画画方面有极高的天赋。画画这个东西,会的人很多,画得好的极少,画得好上加好的,可以说是少而又少,邢先生当然算是少而又少的。
说起我与邢振龄先生的相识,可谓是缘分加缘分。先是我们同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作品,他发表画作,我发表文章,我们虽然不相识,但是彼此应是相知的。我看到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作,给人耳目一新,但不知这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之作。世上无巧不成书,我们在琉璃厂的一个画店偶遇,一聊起来,双方才知原来在报上常看到其名的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真是喜出望外。我眼前这位老者爽朗的笑声溢满整个屋子,给所有的人带来一股朝气。而后更巧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邢先生的画作又刊登在我的文章旁。说这是偶然也好,缘分也吧,真像是上天的安排。
我看了一些关于邢先生的文章,大家都把他说成是丰子恺式的风格,邢先生也同我说过,他确实是受丰子恺的影响。那么丰子恺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画的呢?他认为,一是画的随意;二是源于生活。这两点邢先生确实与丰子恺先生有相近之处。所谓随意就是在不经意中经意,在不讲究处讲究,能达到此境界,才可谓天然雕成。观邢先生画画,是信笔由来,一点不做作,看去好像是不加思考,其实是胸有成竹。说到来源于生活,丰子恺有过一段文字:“我住在万丈红尘的上海,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恍悟春到人间,就作《都会之春》。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就作《买粽子》。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就作《星期六之夜》。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就作《卖花女》。”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再去观丰子恺的画,就能体会得更深入。邢先生也如此,他画一个小孩子给爷爷挠痒痒,画叫《搔痒图》,并附文字于旁:“小竹挠尺把长,怎及小手挠痒痒,我是爷爷痒痒挠,挠在爷爷心坎上。”画面上那位老爷爷开心的笑,跃然纸上。他画母子情,一位老母亲坐在板凳上望着墙上的表,时针指向离七点还很远。邢先生将此画取名叫《相约图》,并题字:“相约七点钟。听儿电话声。”(见图)让人体会母亲盼儿心切,一定不知看过多少次表了,生怕错过了儿子的电话。这些要是没有细心的观察和体会,是绝然画不出来;所以生活成就了邢振龄,给予了他的画的生命。
我不能不提到他给许多友人写的信札。他是一边写一边画,写什么内容就画什么内容,图文并茂。邢先生过去也从事文字工作,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漂亮的文字加上惟妙惟肖的画面,很有一番趣味。他给老外交部长李肇星写了一封信,信的起因是李部长送给他一本诗集,所以他回信道:“在卷首的自序开篇中我看到了您那位‘慈祥老成、博学多才’却是位妙龄姑娘的赵健老师,她将您作文要去作纪念,临终您那本‘充满稚气的小诗和别的作文陪着她在地下安眠……’读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不由地联想起我的小学老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在我离开山东老家来北京时,她向我要了四幅墨竹,其实都是半临摹的儿童画,谁知这不成立的画,老师却只是在每年的春节才拿出来挂。”写到此,邢先生画了一幅一个学生向老师递交作业的场面,其文其画,相得益彰,让人读后倍感亲切。
丰子恺大师与邢振龄先生的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别开了中国画的新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扩展了中国画的内容和画风,但又不失中国画的风采,他们这种对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是前无古人,他们画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但又是以小见大,画的是活的人生,活的社会,所以他们画的是历史,是历史的画,是与历史永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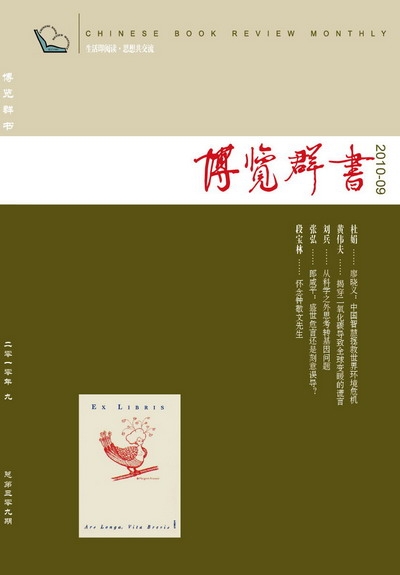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