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渔先生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继承了鲁迅、柏杨等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传统,对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传统思维模式的落后是根本原因,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阅读之后,我想提一点浅见。
一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不能回避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态度,大凡有生命力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既能传承,又能批判,最终归于发展。文化的发展,必然包含继承、批判、发展这三个环节。
在很长的时间里,与周边相比,以五经为核心、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较高的文明位势,即便在军事上败于游牧民族,我们仍然相信自己要比对手更加文明,并为此发展了一套夷夏之辩的理论。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全面崛起的西方世界,我们在多个方面失败,这才促使中国人进行真正的文化反省与批判。国民性批判思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形成了以鲁迅等人为源头的思潮性批判传统。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鲁迅等人所代表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具有特定的进步意义。在世界文明史上,勇于对本民族进行深刻的批判,是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以犹太人为例。在《圣经·旧约》的“先知书”中,对犹太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程度决不亚于鲁迅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并没有摧毁犹太民族的自信心,相反,由于这种批判的持续存在,使得犹太人具有超强的文化承受能力。承受得起自我批判,是一种文明肌体健康的表现。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本民族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判,有如牛虻的叮咬,在特定条件下有利于牛的成长。
二
要评价这本书,应当置之于国民性批判的思潮变化之中加以考察。国民性批判随时代起伏而变化不定。特别是它与民族的自信心具有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要衡量这种思潮的价值,需要设定如下的前提,即这种批判必是诚恳而有又建设性的。
所谓诚恳而又能具有建设性,当有两层涵义。
第一,这种批判是有条件的、特定的和相对的,换言之,这种批判的意义不是无条件的、全面的、绝对的。这种批判必须有很强的时代性,要针对民族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批判,而不是泛滥无边的自我贬斥。国民性批判好比是一种文化治疗术,它旨在治疗疾病,而不是彻底否定病人。
这种批判是相对的。国民性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不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国民性,它只能存在于动态的历史过程之中,特别是存在于与他民族相互交往的真实过程之中,换言之,只有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才能突显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只有动态的历史的国民性,不存在抽象的稳恒不变的国民性。
第二,这种批判最终要有建设性的成果,要与中国历史上具有类似功能的思想传统不断建立关联,不断传承创新的能力,使之不断地加以补充、调整,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脉络之一。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讲,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会对民族的自我醒悟和理性自觉起到积极鞭策的作用。例如,古代犹太对自身的批判最后融入《圣经·旧约》这样的经典作品,成为传世名作。再如,现代的鲁迅先生,其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鲁迅成为现代史上永恒的青年导师,鼓舞了几代知识分子。
与以往的国民性批判相比,这本书的基本前提中似乎注入了具有我们时代特色的内容。在我的印象里,以往的国民性批判总与文化激进派相关联,对传统保守主义予以剧烈的否定。这本书既坚持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同时又对文化保守主义给予了较多的肯定。这大概是这本书的鲜明特点。
这种新意最集中地表现在第一章。在其中,作者对当今流行的几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辩驳。
作者对以下观点进行了辩驳:(1)“封建和专制根源论”;(2)儒家文化根源论;(3)制度、体制根源论。这三种观点是历史上影响极大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很有影响力。
(1)封建专制根源说。在很长时期内这是钦定的正统观点,并与比较简单机械的直线式的世界文明进化观关联在一起。按照某种进化观,人类历史应当经历“古代—中世纪—近代”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模式,将中世纪封建主义看成是为了发展近代化必须彻底根除的前提条件。在行动上,则将政治反封建与民族复兴简单挂钩,形成了某种政治决定论。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立场。
(2)儒家文化根源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儒学曾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批判的共同理由是,儒家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这种批判思潮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上的激进变革,才能取得进步。这本书以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验为依据,对这种儒家文化根源论进行了辩驳。作者的观点吸收了近三十年来有关“亚洲四小龙”、“儒家资本主义”、“韦伯问题”等一系列文化讨论的成果。
一般说,肯定儒家文化的人大多不进行国民性批判,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人往往批判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文化与国民性批判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这本书既进行国民性的批判,也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文化。这在国民性批判史上,似乎是一种新的观点。
作者对保守主义(其中包括儒家文化)作了新的评价。这本书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对犹太民族的极端保守主义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明确指出:“保守是进步的基础,没有保守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进步。”(P69)“中国人的思想不是保守而是僵化。”(P71)从而在保守与批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均衡与张力。
(3)“制度、体制根源论”。将科技创新乏力归咎于制度、体制,可谓是寻常见解,作者对此表示异议。作者以苏联、以色列、德国(纳粹时期)为例,说明制度、体制根源论并不能成立。例如,一方面,作者承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非常严酷的”(P11),另一方面,作者指出苏联在科研乃至在经济发展都曾取得过重大的成就。
总的来看,这本书的种种议论,针对的是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书中所论,均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三
这本书的标题是“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里的“思维批判”针对的是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并对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积极回应了“钱学森之问”:为何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没有流于泛泛的批判,而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全书的重心在于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谓模式,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是一种内在化的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作者呼吁中国人进行思维模式的变革,而这种思维模式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比较自然的结果是要从教育着手。
这些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第七章之中,因此,我想就第七章发表一点评论意见。在我看来,全书似乎有一个基调。这个基点是强调科学,批评人文(作者称之为“文人”)。换言之,在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之间,作者明显地偏向科学。对此,我想提一点商榷意见。
作者提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的缺点是模糊性,缺乏精密性,要克服模糊性,就必须养成科学的精密的思维习惯。对于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是,真正的科技创新过程中,不但需要精密性,还需要模糊性。科学创新的过程,就是精密性与模糊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科学思维能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证明,它的特征是精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径直称其为科学思维;另一种是科学创新(或发现、发明),这种能力事关人的想象力,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我们所说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是两种能力的复杂综合体。一项重要的科学创新,既离不开严谨的、精密的科学实证能力,也离不开弥散开阔、新境迭出的想象力。科技创新的能力是一种综合的能力。科技创新一词,其实有广狭两种涵义。一种是广义的,既包括精密性,又包括发散性。一种是狭义的,它主要指发散性。
怀特海有句名言:“通向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他所说的智慧,指发散性思维方式,而他所说的知识,则指严密的科学推理。
不妨接受怀特海的术语,对科技创新来说,智慧与知识,精密性与发散性,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要获得面对知识的自由,我们需要人文的智慧,这是很难用精密的科学思维所取代的。正如怀特海所说:“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P142)
因此,怀特海富有睿智地指出:“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P127)为了使知识充满活力,就离不开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培养。
四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我们所使用的创新概念。创新似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实际的创新过程,第二,是基本符号系统的思维训练。由于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性,每次创新过程都是极其特殊的个案,因而创新过程是不可教的。但是,人类教育却有一项奇特的本领,能够通过某些基本思维模式的训练,帮助学生提升其思维能力,最终有助于学生针对特殊的情境发挥其创新潜力。在学校里,这种基本的思维模式训练,表现为对语言符号与数学符号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从教育的角度看,一切创新,最终要归结为基本符号系统的传承与创新;或者起码说,应与这种符号系统的创新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关联。
在创新问题上,我个人比较欣赏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以下简称奇氏)的观点,奇氏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创造性——发现和发明的心理学》一书中,他对创造性提出了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
奇氏对“创造性”一词的常见用法进行了分辨,并对创造性一词给予比较清晰的界定。奇氏认为,创造性要体现为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因此,创造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过程,它存在于以专业为特征的群体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个别天才脑中的抽象思维之内。专业群体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拥有某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因此,创造性体现在这种符号系统发生改变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创新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一符号系统的改变过程。
创造性的本质在于一种由相互作用的三要素组成的系统:(1)一种包含符号规则的文化;(2)一个把新奇事物带进符号领域的人;(3)一个能够辩认出并认证其创新性的专家圈子。
在上述三种要素之中,第一方面比较侧重于思维的严谨性,第二方面则需要新奇的想象力,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模糊性、发散性的思维方式。第三则是强调专家圈子的重要性,其实是强调学术传统的重要性。
钱学森先生曾指出:“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引自网络)
想象力是一种发散的思维方式,有时候人们又称作模糊思维,主要指其丰富的联想力、将片断组成协调整体的构思力,以及在弥漫无边的零散点之间建立深刻关联的能力,它与传统人文的思维方式(包括艺术在内)具有深刻的关联。中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出科技创新的大师,大多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古今融会,中西贯通,文理渗透。他们的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丰富而弥漫的想象力,与其深厚的传统人文艺术修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有一个深刻的观点。西蒙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明与创新,都要建立在对这门学科精深的了解之上。一门学科的信息量,总体上与人们精熟一门自然语言所需要的信息量相似。西蒙的观点背后潜藏着这样的一种假设,即知识学科的原型是人类的自然语言。不管某门科学具有何种特殊性,在人类思维最基本的层次上,它们与自然语言具有本质的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有可能是曲折而隐晦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大多数做出重要创新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是比较深厚的。这是因为,人类通过自然语言的训练所获得的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人类一切智能的两大重要原型之一(语言与数学两大原型),而且,与数学原型相比,它更为基本,对生活更加不可或缺。以精密著称的科学,其主要特色是对数学原型的严谨运用,但究其根本而言,它仍然离不开人类的自然语言。这正是传统人文学者擅长的领域。
如果上述粗略的说明能够成立的话,我认为,更稳健的提法是,既要克服传统思维模式不精密、不科学的缺点,也要充分发挥传统人文中模糊思维、形象思维激发人类想象力与联想力的优点。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作者已经打破了国民性批判中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但作者仍然保留了文理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教育问题上,除了在保守与批判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我们还须克服文理之间二元对立,以更全面的稳健心态看待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辩证互动的关系。
各国的工业化大体有两种发展路径。第一类是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政治革命,旧传统与新观念相妥协,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第二类国家,如法国、俄国、德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第二类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特别的曲折。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权掌握在第一类国家的手上,并在全世界形成了一种强势的思潮,人们习惯用第一类国家成功的经验来衡量历史。在历史上,我国走的是第二种路径,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置第二类国家的曲折发展历程于不顾,简单地复制第一条路径的经验。
尽管各国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是,参考这本书对各国科技创新成功原因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一类国家,它们之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成功,从文化上讲,与其灵活而成功地处理了激进与保守的关系、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有关;而科技创新方面之所以曲折,乃是因为在处理激进与保守、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时不够灵活,缺乏弹性。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编辑 陈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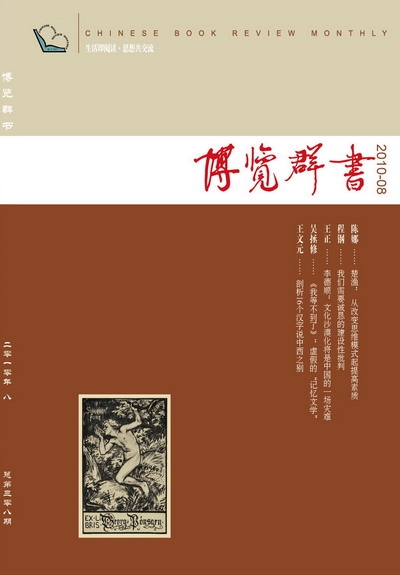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