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适值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独立评论》创刊70周年(1932年5月22日创刊)、与《独立评论》相始终的“忠心的看护妇”(胡适语,见《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家父黎昔非诞辰100周年(黎昔非诞生于1902年5月31日,旧历4月24日),当年10月《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黎昔非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桩尘封的历史真相随之显露。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的编撰、出版的前前后后有些什么启示值得关注呢?
历史的困惑——《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编撰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绍宾《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通栏大标题文章,其中公布了1932年4月24日吴晗致胡适的一封信:
今午同蒋廷黻先生谈话,他说他正在发愁,因为《独立》周报预备在下下星期出版,第一期稿件已齐,却还找不到一个合式的经理人。生因此想起五星期前同黎昔非君到协和来看先生的时候,先生曾提过此事,并问黎君愿否帮忙,就把这话告诉蒋先生,他很高兴,叫生即刻写信,请先生决定并征求昔非同意(他住银匣大丰公寓)。
《人民日报》编者将胡适邀请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那段话全部印成黑体字,而且加了黑体字的按语:“吴晗能够参与机密,为这个反动刊物推荐‘合式的经理人’,显然已是胡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名伙计。”史绍宾这篇文章掀开了黎昔非的故乡广东省兴宁县的“文化大革命”,他立即遭到揪斗、抄家,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反革命分子”,成了全县第一个揪斗对象,而且是“重点对象”。在受尽3年非人的凌辱和折磨之后含冤辞世。
僻处岭南的黎昔非何以被株连而遭此飞来横祸?黎昔非1930年7月毕业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故他们有了师生关系。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恰巧1930年11月胡适也从上海迁平,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于是黎昔非与胡适再度有了师生关系。1932年4月胡适邀请黎昔非帮助他办理《独立评论》,上文所揭就是黎昔非在中国公学的低年级同学、时在清华上学的吴晗当时为斡旋黎昔非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而致胡适的信函。他的“经理人”工作主要是校对、发行以及全部社务工作,由于这个工作极其繁忙,对于他的研究生学业妨碍极大,于是他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但均以“找不到合适的人”而被推辞,迁延至“七七事变”《独立评论》终刊。嗣后他即与其同班同学、曾任胡适家庭教师的罗尔纲以及吴晗三人结伴南行,罗尔纲前往中央研究院、吴晗前往云南大学任职,三位中国公学同学中唯一读了研究生的黎昔非却回到故乡任中学教师。解放后,黎昔非继续在家乡任中学教师,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唯一的“历史问题”就是这段《独立评论》的经历。至于与吴晗,解放后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春风吹进粤东的重峦叠嶂,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对1979年8月24日《人民日报·群众来信摘编·增刊》第52期《平反受“三家村”株连的冤案,阻力在哪?》这份黎昔非子女的上诉信作了批示,于是1979年11月26日兴宁市召开了黎昔非的平反昭雪大会,推倒了横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如果说随着党的拨乱反正政策的胜利,这一历史困惑得以消弭的话,那么另一桩历史的困惑又随之而生。《独立评论》创刊70周年、家父黎昔非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把我们所保存的家父历经劫难而孑遗的一些资料整理出来,辑为一书,自然提上日程。这不仅保存了家父个人的,而且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亦有所裨益的珍贵资料,深惧事易时移,蠹蚀灰灭。于是我着手搜集整理相关资料。
随着编撰工作的深入,我的困惑与日俱增。我儿时就从家母那里知道家父为胡适办理《独立评论》的事情,他们1933-1934年之际在北平结婚,她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待我上学时又从一些中学老师那里听到家父与胡适关系以及胡适曾为家父母担任证婚人等说法,因此我一直对于胡适有一种亲近如同亲人般的感觉。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家父又因为胡适和《独立评论》的问题而遭到迫害,所以在家乡,家父与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关系可谓妇孺皆知。我以为学术界对此也应当是不存疑义的。但是,实际情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对于现代史自然较少关注。当翻阅学术界关于胡适和《独立评论》的论著时,我才发现不仅没有一字提到黎昔非,而且公然说协助胡适办理《独立评论》的是章希吕或罗尔纲等人,或者干脆说《独立评论》根本不存在一个社务部门,如果有什么社务工作的话,也是胡适躬亲其事,不过偶尔找人帮帮忙而已;不仅如此,在胡适本人的文字中也难觅黎昔非的踪影。胡适的日记中除了黎昔非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之前的1931年曾经两处记载了他的事情之外,1932年加入《独立评论》之后便只字皆无了;胡适在1956年出版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回忆《独立评论》创办历史时也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云云,只字不提黎昔非。再查《独立评论》的封面、封底、扉页以及《编后记》等中也都找不到关于黎昔非的片言只字……显然,从胡适到一些学者的笔下,历史的真相被掩盖了。
随着资料搜集的日益丰富和深入,一个令人饶有兴味的现象亦随之而产生,那就是我以前从家母和乡人中所听到的情况不断得到历史资料的印证,而且处处吻合。一个感悟油然而生: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则各种各样的新旧历史资料(口述的、文字的)链条均能够环环相扣,若合符契,左右逢源,无远弗届。但是,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表述却是与历史事实如此大相径庭,而我所面对的是已逝的和在世的权威,本专业、本课题的专家、教授、研究员,乃至一些海外名流、学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定了编撰这本书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即用第一手资料说话。所谓第一手资料,包括当事人和当时人的文字、手稿、书信、日记和图片等。当事人主要有两位,一位是胡适。在编撰这本书过程中发现了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特大号(1935年第151号)上发表的《又大一岁了》中的一段话:
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
这条原始资料,历来写胡适和《独立评论》问题者从未运用。它的发现,不仅颠覆了以往学术界的种种不实之词,以及胡适本人在后来对这个问题的遮盖、掩饰,从而得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另一位当事人就是黎昔非本人。例如至今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昔非在《独立评论》期间致胡适的关于社务工作的三个便笺,1944-1945年间致胡适的三封信,以及我们所保存的他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的日记、1951年7月、1958年4月30日写给组织上的两篇自传……这些资料不仅与上述胡适的相关文字相互印证,而且也被其它相关资料证明是确凿无疑的。
所谓当时人,就是1932年至1937年黎昔非在《独立评论》工作期间的目击者、知情人,包括他的同学如罗尔纲等,他的同乡如林钧南、丁白清等,他在《独立评论》的同事、同乡陈晋祺等,当然还有共同走过这段历程的家母。他们当时的文字和后来的回忆,无不与当事人的记载吻合,起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
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不加个人的感情色彩和评判。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了家父与胡适、与《独立评论》关系的真相,于是幼小心灵中存留下来的亲近感完全破灭;又由于我与书中主人公的父子关系,因此心中的义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智和多年治史的训练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冷静,于是我决定主要是把客观的历史资料摆出来,而由撰稿人、读者根据历史事实做出自己的评判。
历史的复原——《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出版以后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出版以后,其反响之强烈和广泛虽然事先有所估计,但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这种反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中的诸位撰稿人。由于黎昔非其人其事不为学术界所知,而有关他的资料涉及面又比较广泛,除了与胡适、《独立评论》的关系之外,还有从未公布过的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如他的一些《诗经》研究遗稿,他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等,这些资料于《诗经》研究和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研究均有一定价值。于是需要约请有关专家、学者评论这些遗稿和资料,以裨广大读者进一步解读。为此,我将手头掌握的这些资料复印给有关撰稿人。当他们看过有关资料之后,无不为之动容,都表示乐于为这本书撰稿,于是珠玑鸿文络绎见赐。
另一方面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出版之后,各种评介、论述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文章陆续出现,逐渐形成一个热潮,持续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相关文章大约已有五六十篇之多,它们包括学术论文、书评、杂文、综述、介绍、资料等,网络上面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一时难以完全统计。
从众多撰稿人和广大读者、专家学者的反应中,表明他们对于历史真相的复原和所做出的历史评判,有如下一些共识:
1、《独立评论》同当时其它大型刊物一样也是有一个社务部门的,这个社务部门就是被称为“发行所”的单位。民国时期的大报馆、书局普遍有了一套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的出版体制,如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报》,其组织结构大致分为营业部、编辑部、服务部和发行部,在各部门之下还设分部各司其职(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P199、266)。《独立评论》的“发行所”,实际上就是囊括了编辑部之外的其它社务部门,负责《独立评论》的出版、印刷、发行乃至如经营部之下的广告、代派、订阅等业务。并非如有的学者笔下《独立评论》并不存在一个社务部门,有关社务是由胡适躬亲为之的,或者如胡适所轻描淡写的只是住在他家的章希吕帮帮忙即可。历史事实是:“《独立评论》社除了以胡适为首的编辑部外,还存在着以黎昔非为首的社务部——发行所。编辑部和发行所组成了《独立评论》社的两翼两轮,共同推动《独立评论》取得了成功。”(马寒梅《论〈独立评论〉的另一个核心——黎昔非主持的发行所》,《北京社会科学》2007,6)
2、《独立评论》社务部门的负责人是黎昔非。《独立评论》筹备之时胡适即邀请黎昔非担任“经理人”。由于黎昔非的辛勤、负责和超负荷工作,《独立评论》从最初每期印刷2000册,逐步增至14000册,发行至全国各地乃至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随着销路增加,一年多以后社员等捐款便停止了,而且有了结余。1935年已有“银行存款约七八千元”(陈晋祺《我与〈独立评论〉的关系》,《黎昔非与〈独立评论〉》P44)。著名报人戈公振认为报刊之成功端赖经理人,经理人为“一馆之领袖”,需“编辑、营业、印刷”多方面的综合才能方能胜任(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P245)。《独立评论》的成功,与其有了黎昔非这样得力的经理人密不可分。历史事实是,《独立评论》的社务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说是章希吕或罗尔纲等人承担的。
3、《独立评论》的成功是胡适与黎昔非通力合作的产物。《独立评论》由于有了胡适为首的编辑部和与黎昔非为首的社务部门,两个得力的部门密切合作,从而取得了成功,两者缺一不可。诚如唐志勇所说:“《独立评论》之所以办得如此成功,过去只知道胡适等编辑和撰稿人,而不知道还有黎昔非的作用。黎昔非出任该刊经理人,直接关系着《独立评论》的顺利创刊、高质量的出版发行和保质保量、善始善终地存在了5年多时间,表明《独立评论》的成功是胡适等与黎昔非通力合作的产物。”“对于《独立评论》的成功,黎昔非的贡献并不亚于胡适等人。”(唐志勇《〈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史料价值》,《江汉论坛》2005,6)因此,“在肯定《独立评论》乃至胡适为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时,也应当肯定黎昔非在其中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黄波粼《近三十年来国内〈独立评论〉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8,4)
4、胡适与黎昔非的个人品格在《独立评论》问题上形成鲜明对照。学者们一方面高度评价和赞扬黎昔非的品格,“这些材料给出的事实真相是:黎昔非有大志于学术研究,始终并不情愿做《独立评论》那样的事务性工作。他之所以始终没有离开《独立评论》,主要在于‘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笔者按:此为胡适拒绝黎昔非辞职所说的话)。他是为了《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不会因他离开受到影响而留下来的。正是由于他牺牲了自己做学术研究的大好时光,才使《独立评论》得以保质保量、善始善终地出版发行了5年多时间”。(唐志勇《〈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史料价值》,《江汉论坛》2005,6)“尤其是该刊的经理人——胡适的学生黎昔非默默无闻、事无巨细、甘于奉献,使《独立评论》高质出版发行、保质保量、善始善终地存在了5 年多时间。而他自己的学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文革’中也因与胡适和《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而受到无穷迫害,含冤而逝。可以说,黎昔非为《独立评论》而牺牲了自己的毕生”。(黄波粼《近三十年来国内〈独立评论〉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8,4)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于胡适在对待黎昔非和《独立评论》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提出批评和谴责。有的学者指出:“他与胡适的关系又让我们看到胡适性格的另一面。”“从1933年开始黎昔非多次提出卸任,要求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业当中去,都遭到胡适的拒绝。迫于压力,黎昔非提了几次之后,终于不敢再提了,以致放弃自己的研究生学业。黎昔非为《独立评论》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对于他是非常不公的!如果相比较于胡适的另两个学生,这种不公就让人感到不解而终于心里也打抱不平了。”“大家都知道胡适对人慷慨热情,连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只要夸耀他几句,他也乐于帮忙,成人之美,如为他人写学历证明、介绍工作等,故时人都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这里面不乏表面的热情,并有虚荣心作怪在里面。若继续考察黎昔非与胡适的交往,胡适这种性格弱点更是暴露无遗!”(眉睫《从黎昔非的命运看胡适性格的另一面》,《粤海风》2007,6)
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及其悲剧命运,除了胡适个人性格原因之外,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社会变动的反映,它“折射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及胡适等社会精英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建构在那些(由普通民众走向社会中间阶层)普通知识分子艰辛的劳作甚至是被迫默默无闻的‘奉献’基础上的。黎昔非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与社会文化氛围,为全面、深刻考察处在动荡的社会嬗变历程中的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成功的背后不被人注意的(甚至是有意被掩盖)另一面提供了独特视角”(王天根:《从〈独立评论〉经理到〈昙华〉主编的黎昔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2 期,P87-91)。
这些共识,表明被掩盖、歪曲的历史得以还原其真相,这是历史公正性的体现和胜利。直书与曲笔是贯穿于中国史学中的一条主线,虽然曲笔者代有其人或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直书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是最终的胜利者,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定律。
(本文编辑 乔向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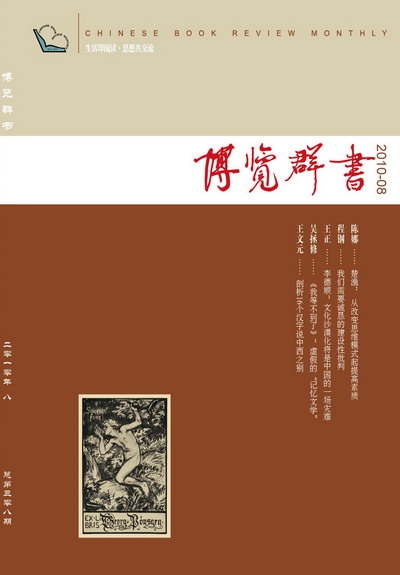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