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8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在东京的一位友人家里,当看到电视里在围绕《冲绳札记》引起的诉讼中大江健三郎胜诉的画面时,我和友人相拥庆祝,这是为公理胜利的喜悦。而接下来,大江氏在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平静——那张脸很难读出笑意——倒让我感觉自己有些滑稽,有些无所适从。因了我的喜悦和无所适从,内心生出想要了解大江氏和《冲绳札记》的急迫。
一
要了解《冲绳札记》,就不得不追溯到“琉球处分”至冲绳战乃至战后的琉球·冲绳那段历史。14世纪确立的琉球王国接受明朝册封,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从事中继贸易,其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就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从“天下统一”到建立幕藩体制的过程中便出现征服琉球的动向。1609年,萨摩藩出兵入侵琉球。因为萨摩藩讨伐琉球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统治琉球而获得琉球对明贸易上的地位,所以在对琉球实行禁武政策的同时,极力保密攻占琉球之事,仍然让琉球以独立王国之形态继续存在。这样,琉球一方面沿袭了明朝的册封体制,一方面逐渐被纳入幕藩体制。也就是说,幕藩体制下琉球的地位,是以东亚册封体制的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到清朝日趋衰落之际,日本决定通过打破册封关系实现其入侵海外企图。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王,完成占领琉球的第一步。1874年日本征讨台湾,制造否定清朝对琉球册封关系的既成事实。次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1879年,强行“废藩置县”,改“琉球”为“冲绳”。甲午战后,日本乘占领台湾之际正式“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至此所完成的“琉球处分”,使日本迈出走向殖民国家的第一步。
如果说“琉球”会唤起近代以来我国知识人的乡愁,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的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冲绳岛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冲绳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遥远而陌生的。那场战争只让我们记住了日本的凶残,或者依稀还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记忆,而10万冲绳岛民的血痕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被一点点地抹拭。
那是1945年3月,美军为掌握整个琉球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建立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开始攻占冲绳岛。为了达到尽量迟滞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美军。当时,驻守冲绳的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官下达“军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军队还下达“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勇自决”的命令。而冲绳岛民认为成为美军的俘虏是最为可耻的事,加之日本军方宣传“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强暴”,并且向岛民提供手榴弹,因此在美军登陆、进攻之际,至此而进行的所有这些准备使得集体自杀一下子成为事实。而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于冲绳人而言的“战后”,只不过是“战火”中的战后:冲绳又成了美军贮藏核武器的基地,并且成为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至越战的战场。自“琉球处分”以来,冲绳不断遭到日本和日本人的弃绝,那里的人们痛苦而执著地斗争着。
二
在围绕《冲绳札记》的诉讼中,大江氏明确表示,作为本土的战后一代,他在该书中想要阐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明治近代化以来,通过“琉球处分”,冲绳人被纳入日本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样的民众意识?如何酿成1945年冲绳战中的悲剧?其二,随着《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离开本土的冲绳在美国军事政治统治下将继续忍受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存续,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其三,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近现代历史中,本土的日本人对冲绳一直持歧视态度;战后,日本本土的和平与繁荣又是以冲绳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大江氏在思考: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并努力寻找答案。这些问题的探讨让大江氏陷入深暗冥晦的精神深渊,陷入瘫软无力和绝望的状态,故而行文处常常出现“深渊”、“无力”、“绝望”等字眼。原因是,那些向冲绳投以歧视目光的、用冲绳巨大的牺牲换来自己的和平、繁荣的本土日本人,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者是血脉相连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尽管属于战后一代,作为本土日本人,他无法自外于那场战争,无法自外于冲绳人的鲜血,冲绳人的牺牲就是对生而受苦的他的惩罚,他被判了罪,他感到苦涩、颤栗、恐怖,但他无法、也不愿意澄清自己存在的无辜,并且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认同冲绳人对自己的拒斥。以自我批判、达成自我认识为契机,他清晰明了地揭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并揭发了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事实。
正是《冲绳札记》中有关集体自杀的记述,使大江氏成了这一场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尽管期间相隔几十年,内心法庭的审判——无论是就过程而言,还是就其意义而言——尚未终结,他却突然被推上世俗法庭的被告席,无法不让人感到担当存在的荒诞,这或许就是被宣告胜诉后的大江氏面无表情的真正理由?在大江氏看来,自“琉球处分”以来,以琉球·冲绳民众之死作为抵押来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这个命题在血腥的冲绳战场清晰有形,并一直绵亘至核战略体制下的今天。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持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和冲绳人而言,本土日本人就罪不可赎,也不存在真正的忏悔。
然而事实上,集体自杀事件的责任人安然无恙地回到二十七度线隔开的追究不到战争责任的日本本土,隐匿在人群中,摇身一变,成了“善良”的市民、慈爱的父亲,直至今天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相反,他们依靠日渐稀薄的、歪曲的记忆将罪孽加以相对化,并不遗余力地篡改过去的事实。比如,把自己对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妇女实施的强奸行为置换成“美丽的瞬间的爱”;又比如说,为了不妨碍军队行动,让军队在作战中没有后顾之忧,冲绳居民自行选择了死亡——这样的死不是很美、很壮烈吗?并且幻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冲绳,当本土的刽子手与冲绳的幸存者再会时,是否有可能沉浸在甘甜的泪水中就此和解了呢?
三
记得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二战后在经历漫长的逃亡生涯后,遭到逮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他建议在公众面前判处自己绞刑,说这是他为了消除德国年轻人内心罪孽的负重而应尽的分内义务。大江氏曾经想象过这样一幅光景:让一个日本人站在虚拟的冲绳法庭上,从他嘴里发出艾希曼说过的话,将“德国”置换成“日本”。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幅画面令人作呕。理由是,冲绳虚拟法庭上的守备队长是相信自己什么罪孽都没有的;而另一方面,日本年轻人的内心并没有如德国年轻人那样背负罪孽的重负。大江氏因而担心:战后的日本在重新一点点地构筑迈向大规模国家犯罪的错误结构。而只要看一看2008年8月15日那天在靖国神社反对大江氏一案审判结果的签名活动的火爆场面,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日本国民因为无知、或者装作无知所置身的可怕险境。
2005年8月,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味间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认为《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岩波书店停止发售,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精神损害补偿。
其实,《冲绳札记》中根本就没出现集体自杀事件责任人的名字。起初,大江氏是通过上地一史写的《冲绳战史》和冲绳时报社编的《钢铁暴风》这两本书了解到关于在冲绳战中发生的集体自杀的详细情况。他原本打算引用《钢铁暴风》中的相关记述,但考虑到其中出现有赤松的名字,最终决定放弃。在大江看来,个人无足轻重,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想象力问题来把握时,才能挖掘出横亘在事件深处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就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皇民化教育渗透到冲绳的国民思想——日本军第三十二军强加于冲绳民众的“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针——列岛的守备队长这种纵向构造,它的形成及其运作形态。如果说置于该纵向构造顶端的守备队长抗拒上级的命令,去阻止集体自杀,从而避免了那场悲剧,大江氏则认为有必要记录下他的名字。然而守备队长只是谨守军纪,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帝国命令,驯服地参与“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充当犯罪国家的代理人——这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最终酿成极权主义之极恶,因此,就不能把引发悲剧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而应该是每个普通的日本人都要接受审判。否则,那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让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人类的未来。
在青年大江氏的思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娜·阿伦特的影响。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以摧毁人的本质相始终。艾希曼的罪恶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端统治摧毁人性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至上的道德命令,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大江氏在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观点,不仅一样具有洞见、隽智,也同样表现出了在黑暗时代勇于承担公共政治的责任。焦点稍有不同的是,阿伦特系统地探讨了极权主义的酝酿、产生、发展的详细过程,以及极权主义下人的责任问题;作为作家的大江氏则侧重探讨上述日本极权主义下的纵向构造,和这种构造中人的——而非某个具体人的——责任问题,这是他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大江氏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还有:对极权主义所造成的罪恶是无法用友情去宽恕、用爱去容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刽子手和受害者是无法在泪水中和解的。当然,那罪恶也无法用恨去复仇。
那么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其一,在《冲绳札记》中并没有涉及原告梅泽裕和赤松嘉次的名字,也没有对他们的个人攻击,他们的名誉怎么就受到损毁了呢?其二,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在二战末期,《冲绳札记》刊行于1970年,为什么时隔几十年后以损坏名誉之罪提起诉讼,实属罕见。为什么在此之前不见抗议,而今突然提起诉讼?其三,在创作《冲绳札记》之前,大江氏尽可能多地阅读了冲绳当地出版社出版的与冲绳有关的书,并走访了冲绳众多的知识分子,其间的所学所闻成为他创作《冲绳札记》的基本资料,也形成了他基本的冲绳观,也就是说,《冲绳札记》并非首次、也不是唯一揭露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书,那么,为什么大江氏会成为被告?
四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场官司的出炉经纬中找到端倪。战败之初的日本文化界曾发出追究文化人战争责任的声音,此后日本的文学艺术着力于凸显普世性或传统日本美的特性,极力淡化“日本鬼子”的形象。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他在获奖仪式上的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就极具象征意义。说到影视,谁又能否认电影《追捕》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中国人的爱情启示录?而我及我那一代人也不可抗拒地领承着《聪明的一休》等作品对我们幼小心灵的滋润。
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责任的清算极不彻底,再加上世纪90年代经济的持续衰退所造成的不安心理,日本政界渐趋保守“新民族主义”抬头,兴起一股右翼势力美化、淡化或是否定侵略战争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以反对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为由,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参与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以此对抗“东京审判史观”。他于2005年4月呼吁开展“冲绳研究课题”,声称要在“战败六十年之际,揭开‘冲绳战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歪曲从军慰安妇的性质的同时,否定冲绳战中日军下达集体自杀的命令。
而在他的系列活动中,也出现了梅泽裕的身影。同年8月5日,梅泽裕和赤松秀一即向大阪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并在二审中出示了日本文部省审查的教科书,认为文部省的立场同样是否定集体自杀命令的真实性。而日本文部省的确于2007年3月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在遭到冲绳11万民众于同年9月29日举行的大型集会抗议之后,仅仅将“强制”改成了非常具有日本官僚特色的“参与”这样暧昧的字眼,还表示:如果送审的出版社要求撤回该稿,可以维持原来的表述。
在自由史观的理论教唆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扶持下,借庞大的30人的律师团壮胆,尚未通读过《冲绳札记》的当年的刽子手理直气壮地走上了法庭,将战时国家机器操纵的犯罪行为巧妙地转换为个人的名誉问题。在历经两次败诉之后,原告并不讳言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声明自己提起诉讼的目的并非仅在挽回个人名誉,而是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敦促通过审查的教科书删除“命令”、“强制”的字眼,重写历史教科书,进而重塑国民的历史认识。
作为“战后的民主主义者”,大江氏反对一切凌驾于民主主义的权威和价值观;对国家主义和天皇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相对于川端康成的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大江氏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词“我在暧昧的日本”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为保守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理念,与加藤周一等人结成“九条会”,在全国各地举办演讲会。
大江氏何以成为被告,还原到时代脉络中,他在冲撞、挑战、触犯逐渐右翼化的日本社会的道德、禁忌、伦理;他暴露了历史真相,颠覆了某些规范,强化了某些意识:而这些,是某些权力所不允许的。
一次民事诉讼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对决,一场挑衅与护卫历史之战。这也说明那一段历史还没有过去,依然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冲绳札记》在与历史同步,或者说,走在了历史的前面:时至2008年10月31日,尽管大江氏在两次审判中获得胜诉,他所要揭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美国和日本政府依然在用强权践踏着冲绳的心。所谓“冲绳的心”是冲绳的和平祈念资料馆的建馆理念,其内涵是:人性的尊严高于一切,坚决反对一切与战争有关的行为,追求和平,格外珍惜发自善良人类灵魂深处的文化遗产。如今,冲绳人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声音淹没在政治家的私念中,淹没在媒体的欲望中,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无法天天持续,日日抚琴而歌总是可能的吧?但愿冲绳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为“艺能之岛”、“歌岛”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
(本文编辑 陈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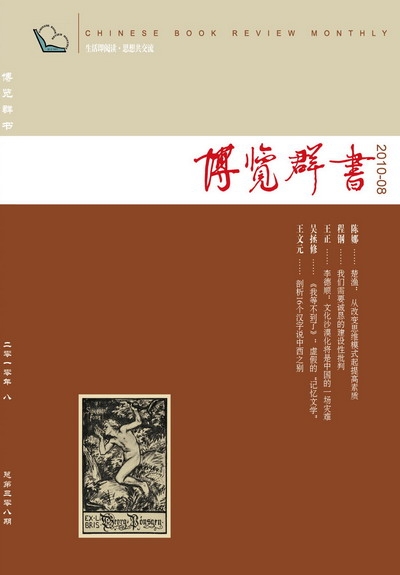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