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九九的新作《疙瘩火》以一方燃烧的火塘为锚点,将童年记忆、家庭悲欢与人性微光编织成一幅火光跃动的温热画卷。在我看来,文本中的“疙瘩火”既是实有之物,也是一种修辞——它是外公悲悯之心的温度,是家庭悲欢聚散的见证,是南曲歌声的岁月回响,更是一代人的精神隐喻。“疙瘩火”,以树兜为薪,树兜作为百丈高树的根本,承载着树木立身生长的力量,唯有坚实、健康且富有生命力的树兜,方能支撑树干、抵御风雨、茁壮成长。《疙瘩火》的叙事,也如燃烧的树兜那样:朴素,温暖,克制,有力。当老树兜在火塘中噼啪作响,火光不仅照亮了沮漳河畔的农舍,更映照着亲情的复杂肌理、代际的碰撞与精神的传承。
“疙瘩火”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其内涵也如有生命的树兜般随情节推进不断生发,从具象的“火”升华为抽象的“情”,最终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在文本的开篇,疙瘩火是童年最直接的温暖来源——外公每天清晨将棉衣烤得“热烘烘”,让“我”在寒冬里感受“蓬松、暖和而干净”的触感,混杂着“太阳和泥土的味道”;火塘边的板栗、红薯、土豆,是兄妹间争抢的美味,也是外公疼爱的具象表达。此时的疙瘩火,是生存层面的温暖,是乡村冬日里抵御严寒的刚需,更是家庭日常“烟火气”的象征。
随着叙事深入,疙瘩火的隐喻意义逐渐凸显。它成为外公生命状态的镜像:外公挖树兜时“赤着胳膊,嶙峋的肋骨清晰可见,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如同疙瘩火燃烧时释放的能量;他为小梨生火、为“我”烤衣服、为小表弟驱散恐惧,始终像火塘里的老树兜,默默燃烧自己,温暖身边的人。当外公身体衰败,“每天早上都捂着胸口,脸膛扭曲,呈现出骇人的黑褐色”,火塘的光也随之黯淡;直到外公离世,疙瘩火“熄灭”,但它留下的温度却未消散,直接内化成了“我”成长、向上、向善的勇气与力量。
如果把《疙瘩火》的行文叙事比喻成一个从燃烧到熄灭的老树兜——疙瘩火,到了故事的终结,我们在燃烧中看见灰烬时,却并不觉得寂灭。即便成为灰烬,在那灰烬里也埋藏着火与热。这得归功于作家九九的叙事——“燃烧有法,熄灭有度”,始终有着“疙瘩火”般的情感温度。
这样的情感温度恰与《文心雕龙·物色》中“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论述相契,作者始终以“含情的眼睛”,凝视作品中的人物。纳博科夫曾说,优秀的文学“是用记忆的碎片编织生命的真相”。作家九九对“疙瘩火”的书写,恰是这种创作观的实践——她将自己对故乡、童年、外公的记忆,化做一个个温热的文字,让“火塘边的时光”超越了个人回忆,成为共通的生命体验。这便是鲁迅所言“把自己投进去”,唯有如此,才能让文中的人物也获得“真生命”。
《疙瘩火》里的人物,也犹如围坐火塘的众生,被火光映照,闪闪烁烁,明暗交织,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划分,而是在亲情的褶皱中勾勒出鲜活的人性。外公是文本的灵魂人物,他不是“完美父亲”的符号,而是一个带着时代与个人局限的普通人——他对舅舅的“娇惯”埋下了代际冲突的种子,面对儿子的不孝时也曾“气得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他的底色始终是温柔与坚韧。他会为会为小梨的遭遇心疼,更会在临终前写下对舅舅的愧疚与期许。外公的“不完美”让这个形象更加真实:他的爱像疙瘩火一样,缓慢、持久、有力。
舅舅的形象则是代际冲突的核心载体,他的“叛逆”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成长创伤的外化。外婆早逝,外公“只知道心疼他,什么事都依着他,却不知道怎么管教他,也没时间跟他沟通”,这种缺失的陪伴与引导,让舅舅成为“长孬了”的树。他逃学、混日子、对父亲恶语相向,甚至将猫咪小梨扔进河里、砸坏小三弦。但文本并未将他塑造成“反派”,而是留下了人性的出口:当小表弟烫伤,他的愤怒里藏着父爱;当看到外公的信,他“眼圈红了”,最终“蹲在地上无声地哽咽”;这也为他多年后的行为埋下了伏笔。他带着孙子给外公烧纸小三弦,唱着曾经厌恶的南曲,完成了对父亲的迟来的和解。舅舅的转变,印证了亲情的“回甘”,即使有过裂痕,血脉里的羁绊终究会在某个时刻唤醒人性的柔软。
“我”的儿童视角有双重功能,既保留了童真的纯粹,也带有“他者”眼光,见证了亲情的复杂。“我”会和哥哥抢板栗、怕花虫子、为小梨的失踪哭泣,这些细节让童年书写更真实生动;同时,“我”也是家庭矛盾的观察者——从不懂舅舅的叛逆,到理解外公的无奈,再到成年后讲述疙瘩火的故事,“我”的成长轨迹,也是对亲情从懵懂到深刻的认知过程。而猫咪小梨,堪称文本的“隐性主角”,它的命运与外公紧密交织:从树洞里被救下,到成为外公的伴儿,再到见证外公的离世,小梨不仅是宠物,更是外公“未被言说的爱”的寄托。外公保护小梨,本质上是保护一份脆弱的生命,这份善意,也映照出他对所有生命的悲悯。
《疙瘩火》的深层主题,藏在“付出式爱”与“渴望被理解”的错位:外公以“为你好”的方式付出,如盖房、还债和对舅舅无原则的娇惯,却忽略了舅舅对陪伴与尊重的需求;舅舅以叛逆反抗父亲的“不理解”,却看不到父亲背后的艰辛。这种错位,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上一代用“生存经验”爱孩子,下一代用“精神需求”质疑爱,直到时光流逝,才读懂那份笨拙的爱。
文化传承是本书的“精神脉络”,南曲与疙瘩火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双生符号。南曲是外公的精神寄托,他用《渔家乐》《悲秋》《数灯》安抚家人的焦虑;即使在草棚里,他也会“唱南曲到深夜”。而南曲的传承,更显韧性:柳柳考上戏剧学院、磨磨教孩子唱南曲、蓉蓉成为南曲传承人。相比之下,疙瘩火的“消失”(后来用电炉、空调取暖)则暗示着乡村生活方式的变迁,但它的“精神内核”并未消失——那份火塘边的温情、家人间的羁绊,被转化为记忆与故事,继续滋养着后代。
对乡村时光流逝的怀想与感伤,是本书的气韵与底色。文中的乡村不是乌托邦,它有贫困、有矛盾,但也有最本真的美好:沮漳河畔的树兜、火塘边的美食、南曲声里的夜晚、孩子们的嬉闹。这些细节构成了乡村生活图景明暗闪烁的丰富肌理,而当“后来的人已不再理会树桩”,当空调代替疙瘩火,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远去,就连“疙瘩火”也成为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怀想,但那朴素,温暖,克制,有力的“疙瘩火”仍在人们心中燃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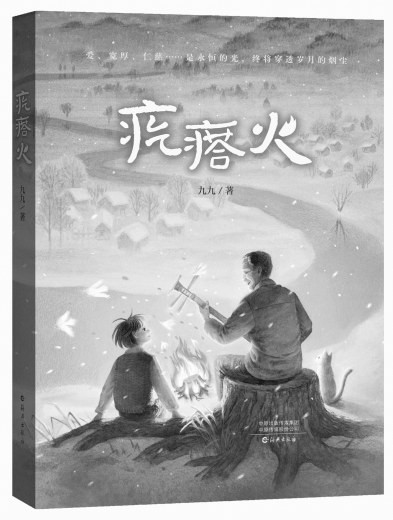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