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
一
近代的印度风起云涌,其中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在人类精神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印度人物,被我们中国人所知道的,至少已有两位重要代表,一位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位是辨喜尊者。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泰戈尔的身份是文学家、诗人;而辨喜则是一位宗教家与神秘主义者。一属诗国之巨擘,一属宗门之雄杰,各自管领各自的星系,各自放射各自的光辉,分明是十九世纪末叶以降,印度乃至人类世界孪生并立的精神重镇。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将辨喜与罗摩克里希纳、甘地作比较,认为三人之中,辨喜的性格最为难解,遭遇也最酷烈,对人类的精神影响也最为深刻,说他“峻烈高耸,犹如被四种灵魂之风吹打的悬崖峭壁”。因辨喜早于泰戈尔成名,很多人愿意将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现身,视作近代印度精神的真正觉醒。最近,由现代印度的大学问僧斯瓦米·尼基拉南达(1895-1973)精心撰述的辨喜的传记《爱与勇气》终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了汉译本。该书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于纽约问世之后,在印度几乎是每两年重印一次,七十余年以来,一直作为学术界研究辨喜这位东方杰出的思想家不可绕过的经典之作。历来被人们争相传颂,是一部洛阳纸贵的名家名传。
辨喜本人虽深深浸润着印度历史与文化的因子,并为印度古老的传统深感自豪,但是,他仍然是在用最现代的方式探索人生与世相的奥秘。尼基拉南达在该传记中将代表古老印度的罗摩克里希纳与代表现代精神的辨喜师徒二人做了一番说明,他说:
“罗摩克里希纳的思想是印度大地的真正产物,他彻底了解印度的性灵传统,而对现代知识一无所知。但是,纳兰(辨喜出家前的名字)则是现代精神的代表。他好奇、敏锐、理性,而且真挚。他拥有一种开放的心智,在接受任何一种结论之前,都要求有合乎理性的证据。纳兰从不允许 自 己被盲目的信仰带走,不被其影响,而且,总是要在理性的熔炉中,检验罗摩克里希纳的一切言行。”
所以,我们可以视辨喜为一座联结印度的历史与未来的卓越桥梁,进而通向了整个崭新的时代,印度的传统也万流归壑,一一进入了他的思想胸廓,几无遗漏,再化作了现代世界的语言,影响巨大。
泰戈尔取径文学,以英语诗集《吉檀迦利》摘走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远扬,但泰戈尔平常并不用英语创作。而辨喜则不同,他完全是有意识去缔造新时代的精神,用英语与整个西方世界对话。最初,他也没有参加世界宗教大会的资格,却千方百计地酝酿绸缪,最后横渡重洋,如愿以偿地参与了1893年于芝加哥召开的人类首届世界宗教议会(The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一席发言,遽成为时代最辉煌的人物之一。这样一位于森林中隐修的托钵僧借此而现身于人类喧嚣的文明世界,可谓蕴蓄谋划已久,最后,也成就了时代的风云激变。10年左右的奔走东西,立下浩大的功业;末后,便造成20世纪波澜壮阔的神秘思想之于文明世界的再度卷起,点燃西方社会持续升温的“东方热”,诱发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不辞倦怠、万里横穿来到印度恒河边由辨喜建立起来的贝鲁尔道院(Belur Math)朝圣。
简言之,辨喜尊者影响之巨,几乎是遍及群侪,他不但影响了印度本土的那些杰出人物,甘地甚至以未能向他成功朝圣而抱憾终生;同时,作为全球化时代早期的豪杰,他影响了列夫· 托尔斯泰、威廉·詹姆斯、马克斯·缪勒、罗曼罗兰、亨利·柏格森、阿诺德·汤因比,以及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著名的发明家特斯拉等人。所以,他确实是罕见的,他跋涉过东西方文明凝定于心灵内在的高度与深度,吸尽西江水,独坐大雄峰;他一旦领悟了梵学之枢机秘义,一朝敷布,如轮之毂,上下四方无不通达,实发大光芒、立大功业之一代巨子也。
二
罗曼罗兰曾视辨喜在西方世界的出现,“是一次伟大的哈奴曼式的跳跃,跳过了分隔两个大陆的巨大海峡”。尽管人们希望了解辨喜作为“东学西渐”的代表,在西方传播印度的吠檀多哲学与瑜伽思想的底细,但困难之处在于,这个人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我们凡间的一切言辞。他短促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精神疑点与谜团,供后来者寻思。一百多年过去了,余波未歇,譬如就在最近,西方学术界又出版一部研究辨喜尊者的生平和思想之作,那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教授露丝·哈里斯(Ruth Harris)所著的《辨喜:世界的导师》 (Guru to the World:the Life and Legacy of Vivekanan⁃da),该书是202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问世的新书。可见,辨喜是经得起人们累年不绝地重复开掘的一座富矿。如今,我们面对的这本由斯瓦米·尼基拉南达书写的辨喜传记,则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流杰作,它之所以引人入胜,因作者本是道门中人,故能够以觉悟者的视角,深刻呈现辨喜生命觉悟的轨迹。它结合辨喜尊者的生平,含摄了他各个阶段的精神成长之过程,包括了至为重要的教 义,借由各 种讲座、信件、诗歌、报道,以及亲身接触过辨喜的时人之回忆,全面展示了辨喜作为一代大师的精神肖 像,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见,传递出了他对精神民主、人文主义与东西方结盟的前瞻性预判,充满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驱者之忧患。气象万千,开阔恢弘,有着不可阻挡的精神性力量,借以对抗与消解时代中暗藏的劫难。关于人类的未来,辨喜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书中写道,早在1895年,辨喜就对克莉丝汀修女说过:“整个欧洲正处于火山的边缘。如果不以性灵精神的洪流将此火浇灭,它必定会爆发出来。”
而在东欧旅行期间,从巴黎到君士坦丁堡沿途一路,他敏锐地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他感到四面八方都弥漫着战争的恶臭,深感震骇,他说道,“欧洲,就是一个巨大的军营,一个火药库!”他直觉到西方地平线上方的亮光,可能不是新黎明的预兆,而是巨大的火葬堆上面将要焚烧起来的血红色火焰。果然,他去世之后,一战爆发;不久,二战再度爆发,人类自相残杀的规模史无前例。可见,辨喜尊者很早就察觉到了摆在西方社会前方的悲剧性景象,还有整个人类面临的深度隔阂与巨大危机。在此,东方的不二论哲学与文化精神,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挽回世道的药石。
所以,辨喜尊者强调行动的吠檀多(Practical Vedanta)。十年之间,历经了无尽的人世苦楚(因他非常重视人间之情分,在与玛丽·黑尔告别之际,深深叹息道:“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竟是如此困难!”),一直致力于人类性灵生命的复苏,故建立了各种道院(Ashra⁃ma)、僧院(Math)与吠檀多中心(Center),在东西方造成了深远融贯的思想影响。
三
如今,我们阅读尼基拉南达的这部传记时,即可深入了解辨喜胸中那海洋一般的知识储备,在书中第十一章,作者写到那一次远洋长途的旅行,辨喜与弟子们一起,于海上纵论天下大势与印度的未来。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大脑,几乎触及到了人类文明的各种话题:基督、佛陀、克里希纳、罗摩克里希纳、民间传说、印度和欧洲的历史、印度社会的堕落及其未来伟大复兴的保证、人类不同的哲学系统和宗教体系,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类似思想主题。
我们知道辨喜尊者的人格之复杂,既有悬崖高处的那种孤独,也有入世的弘大悲心,结合本部传记的阐述,我们综合起来看,大体认为辨喜至少含摄了三重身份:其一、作为哲学家;其二、作为行动家;其三、作为神秘家与人类的先知。他的老师罗摩克里希纳曾给出过一个忠告:“不要草草率率地评价他。人们也许永远不会了解他。”
就我们而言,这里的第二重身份尤为重要,因它意味着救世的悲心,为这个吠舍与首陀罗渐渐唱响主调的新时代,试图提供一条有效的精神出路。辨喜尊者将《薄伽梵歌》的智慧转化为现代人皆可以践行的“行动瑜伽”(Karma Yoga),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条精神道路。它并非静修避世,而是通过 日 常行动实现解脱,将 工作视为祭祀(Work as Worship),在人间实践中贯穿不执与虔信。这种有为法强调行动与 责任,以雄健的勇气直面生活,在琐碎中锤炼爱与智慧,最终抵达内心的源头与人道的通途。辨喜甚至认为,“你们通过踢足球,比通过学习《薄伽梵歌》更靠近天堂。”凸显其借事证道的动态救赎观。
与之相较,佛教对“Karma”的理解偏向负面,故主张无为法解脱,而印度教则赋予“Karma”积极意义。但行动瑜伽的核心仍是吠檀多哲学的现代转化——通过精微心法,在喧嚣中实现力量、智慧与圣爱的统一。于是,将吠檀多哲学转化为“实践的吠檀多”。
如果将这种“有为法”与佛家的“无为法”两者会通而寻觅其印度思想史的根源,也许还得重回《梨俱吠陀》时代的那首著名的“无有歌”(Nāsadīya Sūkta,意为“非无亦非有”),其歌云:
无既非有,有亦非有;无空气界,无远天界。
何物隐藏,藏于何处?谁保护之?深广大水?
四
1879年7月,英国诗人埃德温·阿诺德的《亚洲之光》问世,首次以史诗形式向西方世界生动呈现佛陀的生平与思想,成为19世纪东方文化传播的经典。14年后(1893年),辨喜尊者远渡重洋,在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亮相,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辨喜作为现代印度精神的象征、全球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思想家之一,其地位不亚于阿诺德笔下的佛陀。如果说《亚洲之光》让西方认识了2400年前的觉悟者,那么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深入理解辨喜:正如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辨喜的智慧也表明了“真理永恒,但表达真理必须与时偕行”。
斯瓦米·尼基拉南达的这部传记品质极高,时而汪洋恣肆,时而又精邃深微,复以“觉悟者书写觉悟者”的视角,展现辨喜39年短暂却辉煌的一生。这新时代的圣徒短短39年的寿数,猛烈燃烧,直如凤凰涅槃一般,让吠檀多的智慧之火燃遍了全世界,使得我们得以用新目光来认识一个非佛教的印度。最后,我们就借用汉语世界的梵学大家徐梵澄先生的诗作结:
“弹指流光物外新,千秋圣学未为陈。
此花此叶当前意,此是灵山悟道因。”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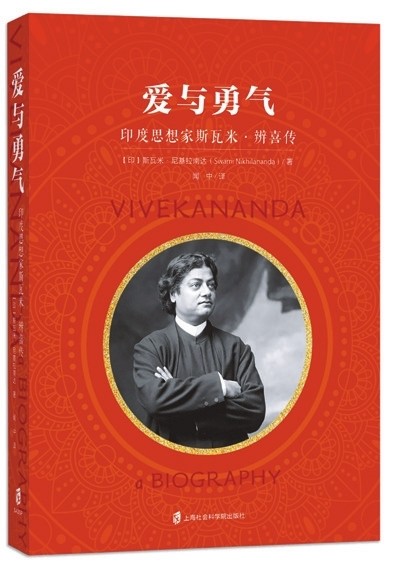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