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
朱利安·巴恩斯的《伊丽莎白·芬奇》是一部难以被简单归类的智性小说,它既是对一位知识女性的精神侧写,也是一场关于历史、记忆与身份的哲学思辨。在这部作品中,巴恩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虚实交织”风格,将虚构叙事、历史论文与人物回忆录糅合,构建出一座跨越时空的文学迷宫,既挑战读者的智性边界,也叩击着现代人面对历史与自我时的困惑。
伊丽莎白·芬奇是全书的核心谜题。作为一位“独立学者”,她的课堂以“严格的乐趣”为原则,拒绝迎合学生的期待,甚至直言“丑话说前头”,这种近乎傲慢的真诚却让包括叙述者尼尔在内的学生为之痴迷。她身着复古服饰,抽着不标明品牌的香烟,以禁欲主义的姿态抵抗时尚与世俗规训。她的思想更充满矛盾:既蔑视“单一性”(如一神论、一夫一妻制),又宣称“爱是一切”;既追求本真生活,又认同“表演是制造真实的完美范例”。
巴恩斯通过尼尔碎片化的回忆,将伊丽莎白·芬奇塑造成一个“未被驯服”的符号。她的形象既是尤里安的精神化身,也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投射——她拒绝被简化,拒绝提供答案,而是通过提问与思辨引导学生直面生活的复杂性,这种塑造手法暗合后现代主义对“确定性”的解构。在小说开篇的课堂场景中,伊丽莎白·芬奇以“手包中的侦探小说”为隐喻,暗示其精神世界的隐秘与反叛。她拒绝使用幻灯片,仅凭“沉静和声音”掌控课堂,这种教学方式本身即是对现代技术依赖的嘲讽。当学生试图用“是否孤独”定义她时,她轻描淡写地回应:“不要误以为我是一个孤独的女人。我是独居,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一辩驳精准切割了社会对独身女性的标签化想象,也揭示了她对语言陷阱的警觉。
小说第二部分插入长达50页的尤里安研究论文,这一结构曾被批评为“打断叙事节奏”。但若细察,尤里安的生平恰是伊丽莎白·芬奇思想的注脚。这位公元4世纪的皇帝生于基督教家庭却皈依异教,在位仅19个月(361年12月至363年6月),临终哀叹“苍白的加利利人胜利了”。他的矛盾性——既是禁欲主义者又热衷祭祀,既宽容基督徒又试图复兴异教——成为伊丽莎白·芬奇口中“模糊性的大师课”,也是巴恩斯探讨历史叙事不可靠性的载体。在伊丽莎白·芬奇的笔记中,她写道:“朱利安不是失败者,而是未被驯服的幽灵。”这一评价呼应了小说对“失败者叙事”的颠覆。尤里安虽败于波斯,但其精神遗产如暗流涌动,恰如伊丽莎白·芬奇的课堂虽终结于死亡,却在尼尔心中种下思辨的火种。巴恩斯借此暗示,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胜负,而在于其作为“未被完成的对话”持续参与当下。
巴恩斯擅长的后现代技法在此书中达到新高度。尼尔作为不可靠叙述者,其传记写作过程不断暴露自身的局限:他沉迷于窥探伊丽莎白·芬奇的私生活(如她是否吸烟、是否独居),却始终无法触及她的精神内核;他试图完成关于尤里安的论文,却因“青涩与颓废”而失败。这种设计迫使读者反思叙事的本质——当伊丽莎白·芬奇的“真实形象”仅存在于他人记忆的拼贴中,历史与传记又何尝不是一种虚构? 小说甚至嵌套了另一层文本:尼尔在火车上阅读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变》,而书中角色同样在读尤里安的故事。这种“镜像中的镜像”结构,既戏仿了学术研究的循环性,也暗示了所有叙事都是“未被完成的论文”。
巴恩斯将全书分为三部,形式上模仿学术论文的“引言-论证-结论”,实则瓦解了传统叙事的闭合性。第三部仅寥寥数页,以尼尔放弃为伊丽莎白·芬奇立传告终——这一“未完成”状态恰恰呼应了她的哲学:“答案会杀死问题,而提问才是永恒的方舟。”《伊丽莎白·芬奇》最终指向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如何在充满矛盾与误读的世界中自处? 她的答案是“严肃的乐趣”——既不屈服于绝对真理,也不堕入虚无。她的形象让人想起巴恩斯在《10½章世界史》中的论断:“爱是我们的方舟,尽管它可能令我们失望”。小说结尾,尼尔在伊丽莎白·芬奇的文档中发现她未发表的札记:“我们对抗的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简化。”这句话成为全书的精神锚点。伊丽莎白·芬奇的遗产不是答案,而是一套思辨工具:她教会学生用怀疑拥抱世界,用矛盾滋养灵魂,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自我与他者的投影。
这部小说或许会让部分读者因智性密度过高却步,但它无疑延续了巴恩斯对文学形式的探索野心。正如伊丽莎白·芬奇的手包中藏着一本侦探小说和整个未被驯服的世界,这本书本身也是一只承载着历史幽灵与思想火种的方舟,邀请读者在不确定的洪流中,以批判与共情并存的姿态,寻找属于自己的“严肃乐趣”。当合上书本,伊丽莎白·芬奇的烟灰似乎仍在空中悬浮,尤里安的叹息仍在耳畔回响。巴恩斯以这场智性盛宴证明:伟大的文学从不提供救赎,但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废墟上起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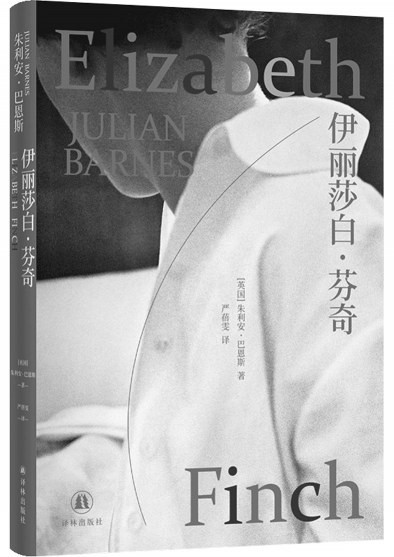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