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哲远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后,在东非沿岸的马林迪(现属肯尼亚,东非重要港口),据传找到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Ahmad ibn Majid,约1432-1500年),并说服他带领自己的葡萄牙船队前往印度。(《阿拉伯人的大航海》,第106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出生在今阿联酋哈伊马角的一个航海家庭,是著名阿拉伯航海家,留下了几十部关于印度洋航海知识的书籍,被誉为“海上雄狮”。尽管当代历史学家认为直接参与达·伽马印度洋航行的领航员另有其人,但也强调伊本-马吉德著作中的航海知识为达·伽马的航行奠定了基础。更早抵达印度洋的郑和,据推测也雇佣了当地航海员作为向导。无论如何,西方人到来前的印度洋,早已是阿拉伯和各族航海家的舞台。光启书局日前出版的乔治·胡拉尼《阿拉伯人的大航海》就是印度洋航海研究的经典作品,内容涉及从史前时代到公元1000年间印度洋东部水域的航海线路以及这一时期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
乔治·胡拉尼(George F. Ho⁃urani,1913-1984)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黎巴嫩基督教家庭。1932年,胡拉尼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古典文学和历史;1937年,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跟随同为黎巴嫩裔的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攻读博士学位。仅仅两年后,胡拉尼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这也正是本书的雏形。1951年,胡拉尼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后,便将学术重心转向了伊斯兰哲学和伦理学,成果斐然。尽管如此,这本以其博士论文完善而成的《阿拉伯人的大航海》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本书在出版后颇受好评,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1991年,英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约翰·卡斯威尔(John Carswell,1931-2023年)在乔治·胡拉尼的弟弟、中东历史学家阿尔伯特 · 胡 拉 尼 (Albert Hourani,1915-1993)的请求下,受命在1951年原版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修订和改版。卡斯威尔兴趣广泛,曾出版过关于中国、伊斯兰世界等地瓷器的书籍。接下任务后,他花费了三年时间,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以增补注释的形式,补充了1951年以来的研究文献,尤其是考古研究成果,对一些地名提供了新的见解,并撰写了新的序言,更新了参考文献、地图和索引。
全书短小精悍,共分三章。在第一章,胡拉尼介绍了前伊斯兰时期红海和波斯湾等地的贸易路线。阿拉伯半岛虽然三面临海,但面临着众多航海挑战:一是缺少造船所需的木材和铁器,二是遍布珊瑚礁的红海北部地区缺少天然港口而且海盗活动频繁。尽管如此,阿拉伯沿海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与腓尼基、印度、希腊等民族保持了海上交流。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阿拉伯人占主导的小型中转港口城市主导了波斯湾贸易(第13页);而阿拉伯半岛西岸更多是被动卷入红海沿岸和地中海东岸的航海活动。在附录中,胡拉尼考证了中国、阿拉伯和古罗马的文献记录,指出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与波斯之间存在直航。
在第二章,胡拉尼关注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一直到十一世纪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动和贸易路线。他指出,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人扩张至地中海沿岸,战争和贸易路线变迁造成了亚历山大的衰落。稍显遗憾的是,胡拉尼和卡斯威尔似乎依然延续了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1937年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中提出的观点,即阿拉伯人的兴起打破了地中海的统一局面,带来了战争和贸易衰退,进而导致了欧洲古典时代的终结(第70页)。被称为“皮朗命题”的这一说法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便遭到了钱币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质疑和挑战。例如1983年,理查德·霍奇斯(Rich⁃ard Hodges)和大 卫 · 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在《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起源:考古学与皮朗 命题》(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一书中,结合考古材料强调伊斯兰势力的扩张是欧洲经济转型的结果,而非原因。固然这些学术论争大多出现在《阿拉伯人的大航海》初版面世之后,但卡斯威尔在90年代的增订版中也没有将其纳入讨论,略显遗憾。
第二章的其余部分,胡拉尼从地中海转移到印度洋的航行活动。在这一相对和平的时期,印度洋与远东和东非海岸的航线和贸易取得大发展。利用中阿文史料,如《旧唐书》《新唐书》、《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 Mamālik)、《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 īn w-al-Hind)等,胡拉尼梳理了从波斯湾到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以及沿线重要港口。但是随着9世纪后半叶唐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先后衰落,阿拉伯商船前往远东的直航也逐渐中断。相比之下,东非和阿拉伯海岸航线的文字记录更少。波斯人在10世纪前主导着这一地区的海上贸易,但这种地位很快随着欧洲蒸汽和燃油动力船只的到来被打破。作为阿拉伯人的胡拉尼,在20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独立浪潮期间修改博士论文时,在书中也展露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当代阿拉伯人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海运现代化,以恢复古代和中世纪的商业地位(第109页)。
在第三章,胡拉尼研究了中世纪印度洋上阿拉伯船只的两大技术特点(船壳板缝合而成、船帆为纵帆)以及导航技术(星盘)和海上生活。胡拉尼注意到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技术借鉴:船体使用的柚木或者椰子木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而使用椰壳纤维的阿拉伯船壳板技术可能传播到了印度等地。关于风帆技术的传播,他通过语言学和史料的考证,推测出拉丁帆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传播轨迹,并指出,“因为如果没有拉丁帆,就不可能有欧洲三桅帆船上的后桅纵帆,也就不可有伟大探险家们的远洋航行”(第138页)。
这本出版于1950年代的专著尽管在时间段(1000年前的历史)、地理范围(以印度洋西部海域为主,偶有涉及地中海以及远东)和研究内容(航海路线和技术)上都非常局限,但为后世的印度洋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布罗代尔名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将海洋史研究带入了更多学者的视野。但学者对印度洋的关注仍然较少,且侧重点多在15世纪之后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活动与征服,少有关注阿拉伯人及其周边民族几千年来在印度洋上的航行活动。胡拉尼在书中旁征博引,强调阿拉伯人在文化科技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全球海洋文明的贡献,一方面反驳了当时欧洲中心的研究视角,回应了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为后续的印度洋航海研究奠定了基础。卡斯威尔在增补版注释中所提供的大量最新研究成果,恰证明了胡拉尼研究的前瞻意义。在胡拉尼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将印度洋研究的视野从航海路线拓展到商业和文化交流,从印度洋拓展到全球史。
在书中,胡拉尼对中国商船在11世纪前参与印度洋贸易持保留态度,而卡斯威尔等人在修订版注释中利用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碎片,强调中国商人和产品在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商船在印度洋的重要地位,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书写中国视角、中国参与的印度洋历史。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印度洋相关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中山大学助理教授陈烨轩的《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利用沉船考古、碑铭和商业文书、传世文献等材料,揭示了当时中国和阿拉伯商人的互相往来;目前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杨斌教授则以全球史视角,研究了海贝这种源于马尔代夫的海洋软体生物在印度洋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广阔陆地世界的流通与影响。
最后值得称赞的是,译者在本书的翻译中做出了大量辛勤工作,不仅翻译了所有注释和参考文献,还寻根究底找到了书中所参考的中文古籍原文。但也有一些地方的翻译或许值得商榷。如译者在序言中所言,在地名翻译中采取了“名从主人”“时空对应”“动态调适”三大原则,在翻译与中国历史文献相关的域外地名时,采取中国古籍所使用的地名和人名。例如,译者将巴格达翻译成报达,将阿拉伯半岛的阿拉比亚人翻译成大食人(第55页),操阿拉伯语的伊朗裔穆斯林也被原作者归类为“大食”人。这可能是译者根据“动态调适”原则,在不同情景下采取不同的名词翻译。但是,一方面这些中文古籍地名考证尚存争议,另一方面,这些稍显混乱的地名翻译给原本相对晦涩的行文带来了更多阅读障碍。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特聘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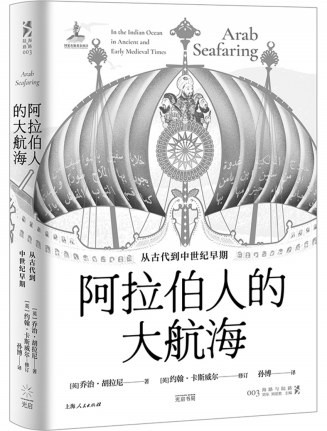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