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舒晋瑜
军旅作家陈歆耕关注稷下学宫这个选题,其实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写毕《蔡京沉浮》,他仍在文史堆里漫游,从家中书柜中翻出早先购买未细读过的有关钱穆的三部书:一为《钱穆与中国文化》,另外两部是钱穆本人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书牵书,牵出了钱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其中有一节“稷下通考”,主要汇集了汉代学者刘向、司马迁等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有一些他的点评文字。“稷下学宫”这个称谓,并未出现在古代的典籍中,古籍记载中多称之为“稷下”“稷下学”“稷下之宫”,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开始正式出现“稷下学宫”这个沿用至今的称谓。让陈歆耕感到震撼,并决定为稷下学宫写一部书的,并不是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在史料中发现的稷下先生们的故事——除了孟子、荀子,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人物,淳于髡、颜斶、鲁仲连等,可谓精彩之极。
“我发现,藏身于史籍中的某些人物故事,其精彩程度,根本不需要通过虚构来呈现。或者说,当代人根本虚构不出当年古人的精彩故事。这也是我痴迷历史非虚构的一个重要因素。”陈歆耕说,稷下学宫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与此同时,在古希腊诞生了柏拉图学园。陈歆耕将其比喻为“双峰并峙”,认为都是人类思想史上不朽的精神殿堂,都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提供了不灭的智慧。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使得他的新作《稷下先生》具备了非同一般的格局和气象。
中华读书报:写作《稷下先生》
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历史严谨性与文学艺术性? 书中既写到孟子、荀子等广为人知的先圣,也挖掘出淳于髡、鲁仲连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还有哪些新发现的史料颠覆了传统认知?
陈歆耕:这是写作历史非虚构作品中,最难解决的一大问题。有的人对这部书的文体归类有疑问,就连电商平台也把它的归类弄错了,把它纳入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榜单中,我觉得这会误导读者,吓跑那些对学术问题不感兴趣的人。我在“序言”中明确说明:“本著不是学术专著……”,此前已经有人写过稷下学研究专著和论文,对学术感兴趣的可以去搜寻。那么这样的文本如何界定呢? 它承续的是司马迁写《史记》的史传文学传统,尽可能地兼容史实的真实性和文学性表述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文心雕龙》中曾有论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牛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说的就是如何情采互凝,文质并重。每位非虚构写作者,在兼容两者上可能呈现的形态会不一样,它跟作者过往写作的实践经验、才情密切相关。我所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地在尊重史实准确性的前提下,让沉睡在典籍中的人物活起来、动起来,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温度,再现人物所处时代的情境,强化某些富有思想意味的关键点:诸如淳于髡发出的狂放笑声、颜斶不肯向前叩拜的那一步、孟子咄咄逼人的“三问”……至于淳于髡、颜斶、鲁仲连这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也并非我刻意挖掘出来的,他们的事迹被散记在《战国策》《史记》等各类典籍中,只要你去读原典就会发现。只是因为他们或因述而不作,或因著述散佚,使得他们的名气不及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那么大。但愿通过这部书,能让更多人知晓这些先贤高光的足迹。
中华读书报:《稷下先生》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很多创新,既有独特见解,又通俗易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创新性继承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如何将古典精髓转化为通俗性语言,对您来说有挑战吗?
陈歆耕:我并未在写作技巧上刻意作什么探索,只是根据搜集到的史料,考虑如何合理地谋篇布局。前提是史料的丰富性,足以构成某些章节。如“面刺寡人”“巅峰对决”“浩然之气”三卷,写了几十个故事,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我所下的功夫是,将这些故事按照逻辑层次,扔进不同的“筐子”里。“面刺寡人”专写稷下先生如何处理与齐国国君的关系;“巅峰对决”是写稷下先生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而“浩然之气”则写稷下先生在解决一些重大疑难问题时,折射出的超人智慧。
这部书的叙事风格,与我此前的两部历史非虚构作品《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蔡京沉浮》相比,并无特别的变化,叙事风格是作者过往写作经验积累与个人性情化合的结果,是否具有个人的标识要看读者的感受。我从来不觉得所谓技巧是可以设计出来的,那应是根据内容寻找最佳表达方式的自然流露。将文言典籍转换为通俗化的表达并不难做到,现在很多古籍都有文白对照的注译版本,这类版本的译文,基本上千篇一律都是按照原文直译,是不追求个性化表达的。而作家创造的价值就在于,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以及调动各种文学修辞手段,来重塑典籍中的人物、故事,师其意而不拘其言。
中华读书报:《稷下先生》卷二《面刺寡人》讲了24个经典故事,各自独立,又有逻辑关联,在主题上层层递进。很多章节也是用人物承载史实,采用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这样的写作有难度吗?
陈歆耕:这是创作此类文本必须要做的案头功夫。如董志翘老师所说的,首先是要“穷尽性”地搜集相关史料,不放过涉及稷下学宫的“一砖一瓦”,关于《孟子》《荀子》,我手头就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些研究论文或文献,虽然其概念性的论述对我毫无用处,但其中提及的史料线索或许对我有帮助,我也会尽可能地加以阅览。这与写报告文学或许有相近之处,报告文学是通过采访获取素材,历史非虚构作品虽然也做实地考察,但主要还是从典籍中获取素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素材的丰富是写好一部书的最基本的前提。
全面掌握史料只是写作的第一步,它帮助我判断已有的素材能否构成一部书,或许写不了一部书,只能写成数千字的短文。第二步是通读所有的史料,并同时对可用的史料来源,做一个便于查阅的索引,在通读的基础上形成全书的框架,此时胸中应该已有“全豹”了。然后再进入实际写作阶段,此时我必须根据每个章节的内容需求,对史料进行第三轮精细的研读消化,然后跳出史料,将素材揉碎,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干这样的“勾当”不全靠才情,案头功夫确实非常辛苦,是一个体脑并用的力气活儿。
中华读书报:“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同时他们又深度参与政治,您如何看待稷下学宫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陈歆耕:“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宫极度包容的学术环境而引发的现象,也可以说是稷下学宫的办学模式所带来的效应。并非人人皆可学而优则“仕”,进入行政的实际操作层面,需要管仲、晏婴、王安石那样的综合能力,但进入不了政坛,也可以将个体的思想、智慧尽情地迸放。即便是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无聊话题,如“鸡有三只脚”“卵有毛”等,也照样可以进入“啧室”进行争鸣探讨。正因如此,稷下学宫才成为士人们向往的殿堂,才会成为“百家飚骇”的学术高地。“稷下学”实际就是“诸子学”,个人认为并不完全等同于“齐文化”。“齐文化”的主流学派是“黄老学”,代表作是《管子》,而“稷下学”兼容并包了儒、道、墨、名、法、阴阳等各派学说。责编曾跟我探讨,能否写一节稷下学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我也尝试以“居高声自远”为题写了数千字,但还是放弃了。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等于是要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仅仅写其中某一家的古今流变,就足以写成一部专著,还未必能说清楚。
中华读书报:批评家、报告文学家的多重身份为写作带来什么?
陈歆耕:评论的写作,强化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而报告文学的写作,则使我在情采互凝、文质并重上有所借鉴。
中华读书报:近十多年,您专注于长篇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写出了《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蔡京沉浮》《稷下先生》,这样的写作轨迹是自然形成的吗? 您选择传主的标准是什么?
陈歆耕:《剑魂箫韵:龚自珍传》是作家出版社“120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中的一部,算半个命题作文。说“半个”,是指涉足这个选题有受邀的因素,但传主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我觉得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清代第一诗文大家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其实,这是晚清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其综合成就绝对处于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名人的第一序列。关于《蔡京沉浮》和《稷下先生》的选题,都是在日常的典籍阅读中读出来的。在遇到某一个“点”时,内心受到触动或震动,我常常会驻足停留,进一步搜集相关的史料,根据史料的丰富性来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另换选题。我喜欢没有人触碰过的新领域,不喜欢在别人耕过多遍的地上再去翻土,“现实感”是决定选题的重要因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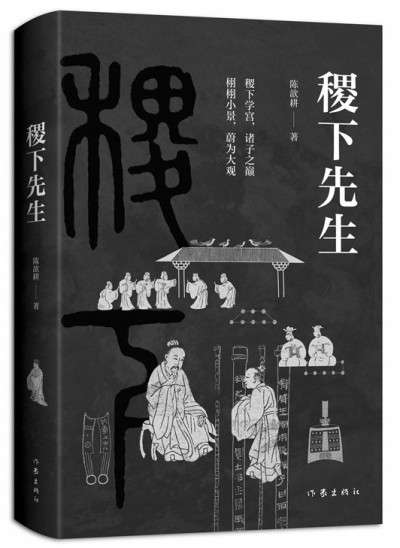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